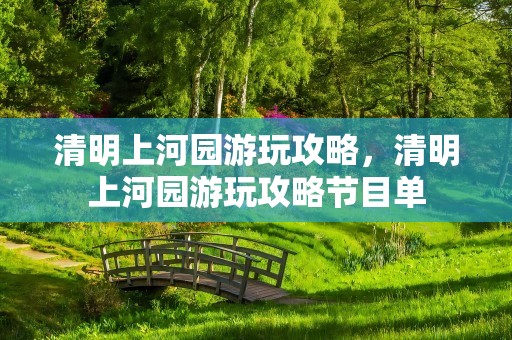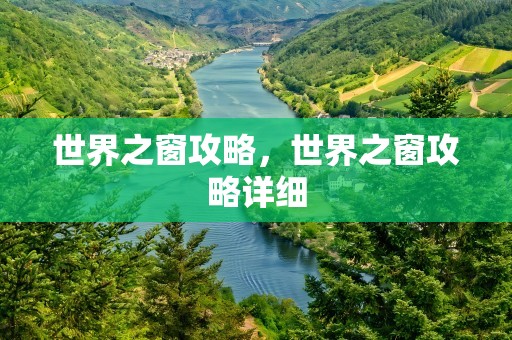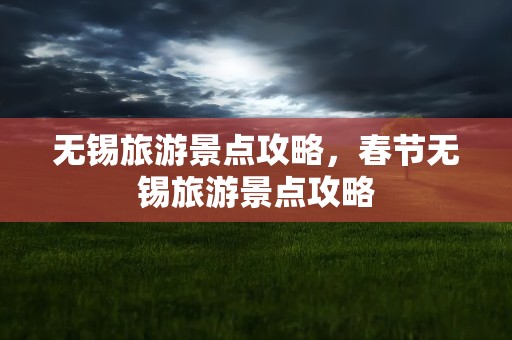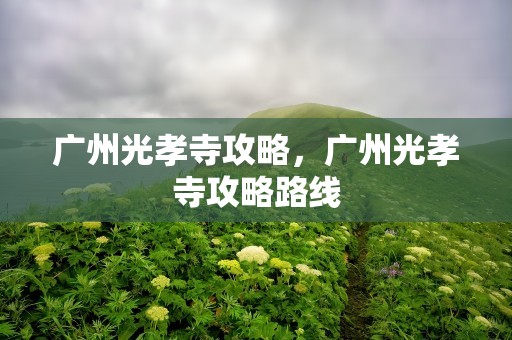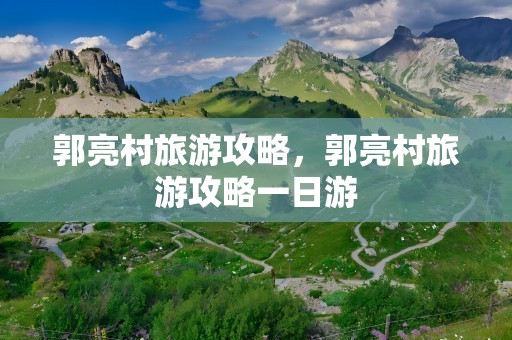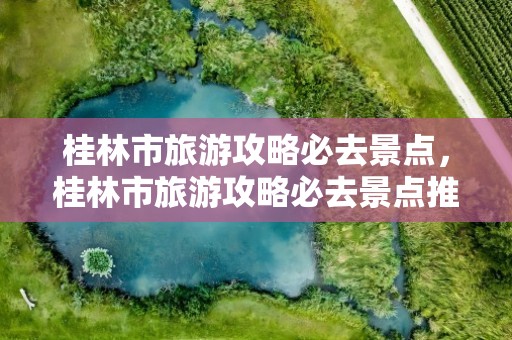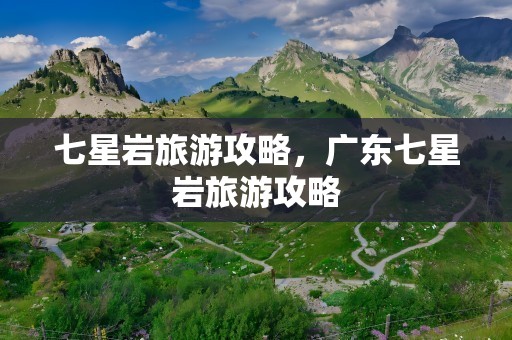昆仑山脉是万山之祖、龙脉之宗,但“此昆仑非彼昆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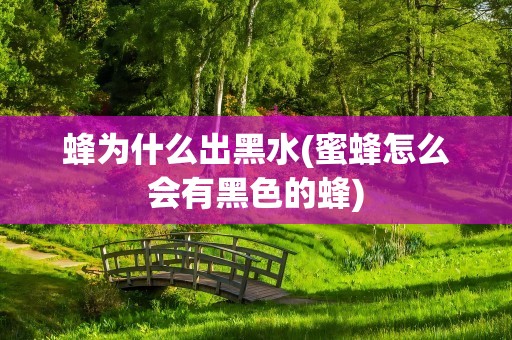
奇书《山海经》中描述的“古昆仑”并非是现如今位于帕米尔高原的昆仑山脉,准确的说“古昆仑”是一座包含了山岭的大山,而“昆仑山脉”则是由山岭、山谷、山峰组成的庞大山脉,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却相差万里。
昆仑山自古以来被中华民族誉为仙山,是千古神话的源头,但是有关于昆仑山的具体方位却令古今学者争论了2000多年。
根据笔者查阅资料所知,自春秋时期开始古昆仑山便成为了历朝历代寻找的对象,屈原在《天问》中问道:“昆仑悬圃,其居安在?”
到了秦汉时期古人认为于阗的南山才是古昆仑山,但是这一看法遭到了史学家司马迁的强烈质疑,西晋后期,凉州王张骏认为祁连山才是古昆仑,包括唐朝以及至今许多学者赞同“祁连山是古昆仑”的观点。
清代乾隆皇帝平定西藏后,又稀里糊涂将古昆仑山改回了于阗的南山,于是对于古昆仑山的定位又回到了原点。
到了现代,随着网络信息化的普及,广大网友们对“古昆仑”的具体位置更是众说纷纭,又是山东泰山、又是陕西终南山、更有甚者将位于非洲大陆的乞力马扎罗山都卷进来了,最可笑的是居然说古昆仑山在月球上,月球只有火山和环形坑,难不成华夏民族的发源地在环形坑中?
探究古昆仑的具体位置,则必须从《山海经》入手,根据《山海经》记载: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西海之南”指西安南郊的古三门湖,“流沙之滨”指古三门消失后遗留的沙地,“赤水之湖”则位于贵州遵义,“黑水之前”指位于蓝田的灞水。
按照《山海经》所述,古昆仑应该在陕西省西安市的蓝田县内,而2449米的箭峪岭则极有可能是古昆仑之丘的主要山峰。首先,华夏祖先之一“蓝田猿人”生活在蓝田县灞河中下游,这与“古昆仑”是人类发源地的说法不谋而合,其次蓝田是被“神垂青”的地方,古代神话中的三位人皇“华胥、伏羲、女娲”都出自于蓝田,这又与“古昆仑”是中国古神话发源地完美契合。
再来,根据古籍《水经注·河水一》、《东京赋》、《昆仑丘赞》综合所述,古昆仑山由无座高耸入云的山峰所组成,分别是:古“天柱”—草链岭(海拔2645.8米位于秦岭)古“玄圃”—箭峪岭(海拔2449米位于蓝田)古“华盖”—玉山(海拔2311米位于蓝田)古“荆山”—风雩山(海拔1814米位于蓝田)古“阆风台”—云台山(海拔2224.1米位于蓝田)另外,传说中古昆仑山居住着掌管瑶池的西王母,而在陕北定边县发现的汉墓壁画详细的记录了西王母坐在古昆仑五山之巅的顶峰的画面
陕北是陕西省的北部,在陕北发现西王母壁画恰好证明了古昆仑在陕西蓝田的论证。
综合古文记载、壁画记载、人类起源、神话起源、山行地貌五大因素来判断,古昆仑最有可能位于蓝田,而上文所列出的五个山岭,则是组成古昆仑山的五大山峰。
非洲的乞力马扎罗山不可能是华夏文明的发源地,月球更不可能,月亮上住的也不是西王母。目前为止只有陕西蓝田群山才是最为靠谱的“古昆仑”。
昆仑山是万山之祖,其传说起源出自《山海经》。《山海经》中记载的的昆仑山又名昆仑丘、昆仑虚,是中国神话中最神奇、最神秘的一座神山。神话中的昆仑山和现实中的昆仑山脉是两个概念。现实中的昆仑山是汉武帝命名的,“昆仑”二字正是从《山海经》中借用的。传说昆仑是天帝在人间的行宫,又是中天之柱,其上可直通天界,凡人登上昆仑山,即可长生不死。山上生活着很多神奇的动物,比如长有四只角的山羊,像蜜蜂一样蜇人的怪鸟,还有很多神奇的植物。
《山海经》中对昆仑山的位置是这样描述的“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从这点去看古人描述的昆仑山肯定不是月球,现实中也找不到相似的地方。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很多人都认为,《山海经》是一部神话小说故事,其中的昆仑山肯定也是想象出来的。但近些年随着书中描绘的生物逐渐被生物学家找到原型,而且分布在全球各地,世人于是对书中内容也抱有谨慎的态度。而且地理学家也发现书中描绘的地理概貌与大陆板块飘移之前的地貌十分相似,所以昆仑山也不一定在中国,目前就有不少人认为《山海经》中的昆仑山在非洲,也就是乞力马扎罗山。
中国众多专家经过考证后一致认为《山海经》是一部神话政治历史书,书的作者也不止一人,从上古尧舜禹时代到秦汉时期都有创作者加入,书中所述大都依据现实情况演化而来,只不过由于时间久远,文本残缺不全,后人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所以书中所描绘的昆仑山早已不是原先的模样,仅根据目前所知道的线索是无法找到其具体位置的,但可以肯定的是昆仑山不是月球。
从夏商周到现代,中国的政治地域从昆仑山脉由西向东,从北至南迁徙。作为主流观点(三星堆文化不谈)的中华文化发源地的古昆仑自然在中华文明中享有崇高的地位。中国古代神话中的西天应该与古昆仑有关。
但是要说月球就是西天这个结论是可以否定的。月球在中国神话里代表的是广寒宫,是后羿的妻子嫦娥所居之处。而且“嫦娥奔月”这个成语已经很明确的告诉了我们在中国神话里西天和月亮是区别开的。
不过按照中国神话里的描述,月亮是属于西天的一部分。同样月亮也可以代表西天的神圣与神秘。
月球乃广寒宫,昆仑为西天王母道场,两个根本不是同一个地方,上古昆仑是万仙的故乡,月亮只是少数一两个神仙的道场而已,两者之间的地位相差甚多,月亮最多算是一个洞府,昆仑为世界的中心,这里有三清中最强大的元始天尊,这里有西天王母,这里是天帝的行宫,远不是月亮可以比拟的。
传说中的昆仑是上古时代所有神仙都向往的地方,在最早的山海经记载昆仑上面居住着各种修炼得道的神,而在后世的文献中描述,上古昆仑居住的不只是神还有许多仙,曾经的那些飞禽走兽和奇花仙树都被各种各样的宫殿取代,各种传说非常多,但是以道教正神西天王母道场流传最广,王母掌管着修仙者成仙登引的责任。
还有传说人皇伏羲其实也是出自昆仑,三清的元始天尊也长居昆仑道场,昆仑的地位可谓是三界中心之一,传说中昆仑是中国本土道教的发源地,而中国的仙神文化中自然以道教为主,道教为我们的本土文化的结晶,佛教为外来户在我国文化中佛教的存在并不归昆仑管辖。
月亮为嫦娥的居住地,嫦娥为神话女仙之一,在中国的文化中嫦娥的地位远远低于王母,月亮属于一个普通的修炼洞府之一,根本不能跟昆仑这样神圣的地位相提并论,月亮归昆仑管辖,嫦娥乃是三界普通的女仙之一,三界之中所有的女仙都归王母管辖,从这方面来看就知道月亮和昆仑之间的差距,如果月亮是昆仑那王母就住月亮上了月亮就成为万仙故乡了,但是在中国仙神文化中月亮的地位是比较低的。
当然我们现在的昆仑山并非上古昆仑,但是不管是上古传说中的昆仑还是现在现实中的昆仑山脉,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同时都是被认定为神圣之地,古昆仑为万山之主,现在的昆仑也一样,是我们中华龙脉的源头,称为中华龙脉的祖脉,在古代的昆仑为万仙故乡中华神山,现在的昆仑地位也是非常神圣的。
《山海经》中关于昆仑山的记载:
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处之。其下有弱水之渊环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辄然。有人戴胜,虎齿,有豹尾,穴处,名曰西王母。此山万物尽有。(大荒西经)
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而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海内西经)
《山海经》是一部非常光怪陆离的小说著作,里面记载着各种各样的事物至今让人们研究不懂,现在人们对于这本书的真实性还是存在疑问,虽然这本书真的存在,但是现在人们还以为能够写出这本书的人是真的不一般,因为要说没有记载吧,还能够从现实生活中找到。
有个地方非常的生产休闲的得道的人,这个地方就是“昆仑”其实能够写出昆仑这个名字一般都是从《山海经》中看到的,所以说昆仑就成为了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那有人可能就要问了,书中记载的昆仑莫不是现在的昆仑山,其实并不然,现在的昆仑山脉大家都知道在西藏。
但是在古代那个地方是没有人存在的,尤其是编纂《山海经》的人,更加的不可能跑到那里去,只不过后来人们根据《山海经》取得名字,其实古人们眼中的昆仑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月亮,当时人们记载昆仑上有神仙,说明古人可能登上过月球,书中记载的是有一石梯连接着陆地和昆仑,那时候的昆仑还是在海上。
我们可能就要有疑问了,石梯纯属就是古人瞎编的了,怎么可能存在呢,但是看过《圣经》的人相信会有印象,因为在《圣经》中记载人们为了看到神也修建了一个非常高的塔,一直通到天上,这难道是巧合吗,真的具有可考性,毕竟两者的相似度太高了。这个石梯就是“万仞山”,
月亮就是“古昆仑”,“中国人”曾是最接近“神”的人种。
可以百度昆仑丘,昆仑虚
汉族尚红,至今有中国红之说,但满族尚白,如满族最早的对联都用白色,大金国的时候也尚白。如果从世界各民族分析,尚白的是主流,如西方各民族也尚白,如婚礼的婚纱都是用白色,而红色被认为战争和流血。下边是专家就满族尚白的论述。
满族尚白艺术形式美解读
阎丽杰1,左宏阁2
(1.沈阳大学文化传媒学院,辽宁沈阳110044;2.北方民族大学文史学院,宁夏银川750021)
摘要:满族自古有尚白习俗,从而使满族的艺术形式美具有鲜明的色彩特征。满族艺术尚白和满族的历史文化、社会生活实践、民族习俗有密切的关系。满族艺术尚白的特点是满族深层社会心理的艺术表现。
关键词:满族;尚白艺术;民族心理
崇尚白色是满族艺术形式美的重要特征之一。白色尽管是艺术形式符号,但崇尚白色却是人们在长期生活实践中情感积淀的对象化外显,白色被满族人赋予了丰富的情感想象,满族人通过白色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
满族自古就有尚白习俗。满族先世靺鞨建立渤海国,白色成为满族先世的部族特征。“完颜部多尚白。”[1](1396)“金俗好衣白。”[2](552)《满文老档》记载满族用白马祭天。满族自古就把白色作为尊贵的象征,并保留了尚白习俗。
一
(一)满族的生息之地常年冰雪覆盖
满族以长白山为发祥地,号称“白山黑水”。长白山是东北的主要山脉,满语称长白山为“果勒敏珊延阿林”。长白山的主峰白头山直插云天。唐朝称长白山为“太白山”,金朝时始称“长白山”。古时记载长白山“山体皆沙石,而草木不生,积雪四时不消,白头之名,似以此也”[3](1)。从肃慎到满族,满族在长白山繁衍生息了三千余年。长白山的丰富资源成为满族重要的衣食来源。满族人喜爱长白山,敬奉长白山。满族尚白习俗和长白山情结有密切的关系。“个人无意识有一个重要而又有趣的特征,那就是,一组一组的心理内容可以聚集在一起,形成一簇心理丛。”[4](35)由于满族世世代代在白色的环境中生活,白色与满族的和平生活形成了固定的联系。长白山冬季长、夏季短,冬令时节,大雪封山,坚冰锁河,银装素裹,玉树琼花,一片冰雪的白色世界。满族在白色中积淀了浓厚的情感,这与满族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满族的民间信仰中崇拜白色
满族先世认为白色是驱魔洁世的吉祥之色,萨满祭祀时往往穿白色衣服。满族萨满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中女神用白色神花战胜了恶魔。天神阿布卡赫赫被抓,天要塌陷,日月无光,天鸟地兽相继死亡,在千钧一发时刻,者固鲁女神们化作了一朵芳香四散、洁白美丽的白芍药花星。恶魔们争抢着摘白芍药花,花朵突然变成千万条光箭,射向恶魔的眼睛,恶魔痛得满地打滚,逃回了地穴。因此,满族人无论戴花、插花、贴窗花、雕冰花,都喜欢白芍药花。
在萨满教中,白色的雪花也是满族人膜拜的对象。“雪花,也是白色的,恰是阿布卡赫赫剪成的,可以驱魔洁世,代代吉祥。”[5](34)满族雪坛主祭神尼莫妈妈身披洁白皮斗篷,骑着豹花点的白色母鹿。满族先人热情地讴歌雪花:“瑞雪降临了,吉祥的雪呀,幸福的雪呀,富庶的雪呀,灾难远遁,兽群繁盛。”满族的萨满教认为白色的雪花可以给人们带来吉祥。
满族的萨满教离不开白色。满族的线锁是用白绫制成。满族同族祭星,要用白羊、白马、白兔皮做祭服,用白石垒灶烤肉,“山坡上的祭坛是用洁白的冰砌成的,通往祭坛的梯子也是用冰制的,祭坛的左后方有冰砌的星塔,内有长明兽头灯。星塔前竖立着冰雕成的神兽偶,称为护塔神兽”[5](53)。
(三)满族的渔猎文化影响深远
满族尚白习俗和满族的渔猎文化有关,最直接的原因是有利于获取猎物。“女真及其先世,长期在冰雪环境中从事狩猎,白衣与冰雪同色,便于靠近被猎取的禽兽,提高命中率,具有保护色的作用。世代因袭,遂成尚白之俗。”[6](65)满族的先人在长白山林海雪原中狩猎、伐木、砍柴,对洁白的冰雪怀有深厚的感情[3](2)。狩猎结束后需要安全往返,而安全往返的首要条件是辨方向、明路线,其依据是猎人发现白色的鸟屎。白鸟屎也称“雀书”,是吉祥的预兆,也是满族猎人的路标。有的满族猎人在某棵树上砍掉一块树皮,露出白茬,也可以成为路标。满族先人狩猎要借助于猎鹰海东青,海东青以有纯白的“玉爪”者为上品。满族猎取的貂皮以毛长三寸的“千金白”为稀珍。可见,满族的渔猎文化和白色有着不解的渊源。
(四)满族的采摘习俗中注重白色
满族经济是从狩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过渡的。满族先人大宗的经济来源是采集,主要有人参、蘑菇、蜂蜜、白附子、蜜蜡、松子、榛子仁、菱仁、桦皮、珍珠、白芍药、海象牙、盐等。这些采集物有一个共同的特征——色彩为白色。如白色桦树皮有重要的用途:桦皮筐成为满族人重要的生活生产工具,可以用来挖人参、装松子、拣蘑菇、采药材等等;桦树皮还可以苫房顶,制成纸张、桦皮碗、桦皮盆、筷子盒、茶叶盒、针线盒、引诱野兽的喇叭、捕鱼的浮标、牛笼头等等。另外,满族自古有采食白芍药之俗。《松漠纪闻》记载:“女真多白芍药花,皆野生,绝无红色。好事之家,采其芽为菜,以面煎之。凡待宾客斋素则用,其味脆美,可以久留。”[6](278)
(五)满族的生产工具多为白色
满族先民对白色金属的需求导致了独特的审美。《金史·太祖本纪》记载:“辽以宾铁为号,取其坚也。宾铁虽坚,终亦变坏,惟金不变不坏。金之色白,完颜部色尚白。”[1](17)明朝时的女真人要交铁赋,女真人用貂皮与李朝换回牛铁等必需品,牛以厚其农,铁以利其兵。满族先民最大的贸易品是铁。各部女真由于缺乏铁的来源,陷入男无铧铲、女无针剪的困难局面。满族先人以白色金属为美,因此,满族好的生产工具大多是白色的。
二
尚白艺术是满族民众长期审美实践的结果,是满族群众集体审美意识的结晶。它不是某一个天才艺术家独到的发现和创作,而是满族民众自觉自愿、不知不觉、超越时空的一种创作,满族民众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创作,而仅仅把它看作是生活中的一种必需品,看作是生活的一种程式化的遵循。
满族尚白艺术兼有民俗生活和艺术的二重性,是满族民俗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满族民俗生活中的必有之物,同时,满族尚白艺术也是满族的一种民间艺术。这种艺术是非专业艺术家创作的,艺术媒介往往是生活中信手拈来之物,包括树叶、苞米窝、桦树皮、鱼皮等。满族艺术散发着浓郁的生活气息。满族艺术作品往往取材于生活中的用品。满族艺术媒介与满族民俗生活、地域气候密切相连。
(一)满族尚白艺术在萨满服饰中有鲜明表现
满族星祭神服是白色对襟的上衣,衣襟上缀饰七颗黄黑色星星,左衣襟有三颗星星,右衣襟有四颗星星。萨满海祭神服是白色缀有黑白图案,黑白图案位于海祭神服的领口周围、衣襟下摆、袖肘部位。萨满祭的骨披肩、骨裙都用白色骨片装点而成。萨满鹰祭大白鹰舞曲的表演服饰为白色神鹰。萨满神偶、冰偶、鹰神神偶、医病神偶、神鼓、九千岁面具等都为白色。“往昔,在满族背灯祭时,萨满要身围白裙,摇动腰铃或洪鸟(铃),两肘扇动,象征布星女神卧位多妈妈的非凡来历,她是创世之姊妹祖之一,她人身鸟翅,身穿白色羽皮袍,背着装满星星的小皮口袋。”[5](51)可见,满族的萨满教祭祀当中注重白色,彰显白色。满族绣花女神伊尔哈生前绣出的花都有生命,死后化作雪白的大石头,哪个姑娘坐到这个白石头上就会自动绣花。绣花女神变成白色石头不是随意为之,而是满族传统的审美习俗使然。
(二)满族尚白艺术在口承文学中有大量表现
满族人喜爱的许多土特产都是白色的,食物如人参、桦树、蘑菇、蚕蛹、豆腐,服饰如萨满祭祀服饰,游戏用品如嘎拉哈等。满族人喜爱的笊篱姑娘就姓白,戴着白花。满族的许多神话传说都描写了这些白色的土特产。《罕王赏参》《人参蜜》《扇子参》《棒槌姑娘》《棒槌鸟与达六哥鸟》《参女搭车》《人参泪》《桦皮篓》《桦树精求亲》《桦树姑娘》《养蚕姑娘》《蚕姑姑》《不爱财的豆腐儿》《白云格格》,这些满族说部都与白色有关,表达了满族人对白色的喜爱。
(三)满族尚白艺术在剪纸中有重要表现
满族旧俗春联用白,丧事用红。满族白色剪纸图案多为神偶、动物、花卉,表现了满族丰富的民俗生活,民族狩猎生活、萨满宗教、英雄故事、饮食习俗等都在满族剪纸中有所表现。另外,满族人还用风干的白色苞米窝剪纸。苞米窝即苞米叶,苞米叶剪纸独具特色。苞米叶剪纸采用干燥的苞米棒里面的2至3层叶片,一般叶宽10至15厘米,最长可达17厘米。苞米叶剪纸粗犷简括,自然古朴,纹理天成,取材方便,生态环保,图案吉祥。
满族祖宗板上的满文挂笺为白色。祖宗板上的白色挂笺大体呈长方形,下部为锯齿状穗子,中下部为蜂巢状镂空底子,上面刻有满文。白色挂笺上的满文为“佛尔郭出课”,汉语的意思为“奇瑞”,意在歌颂祖宗的功德。挂笺洁白无瑕,庄重肃穆,用来祭祖。祖宗板上的白色挂笺为三至七张不等。
(四)白色成为满族人重要的审美标准
白色成为满族人判断美的重要标准。满族说部《萨布素将军传》中描写萨布素“身板像小白桦树一样挺拔。”[7](4)“那女子的面容,娇嫩得就像山坡上刚要开放的芍药花。”[7](125)白云格格穿的衣服之所以美,是因为她的衣服是由“九十九朵雪花云织成的银花衫”。雪祭的《报祭词》中歌颂圣洁的雪:“阖族集众虔诚雪祭。九层天上的雪呀,圣洁的雪呀,吉祥的雪呀,阿布卡格赫赐给人间。”[5](67)满族歌颂雪,洁白的雪带给人们子孙绵延,福寿无疆的幸福生活。
三
色彩能引起人不同的生理与心理感受。满族人对于白色的喜爱,与满族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满族栖息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的冷暖对满族民族心理有很大的影响。白山黑水、冰天雪地的生活环境使得白色已经在满族人的潜意识中积淀、抽象,逐渐成为和平的符号。白山黑水冬季漫长,夏季短暂。常年与冰天雪地打交道,满族人生活生产环境和白色结下了不解之缘。白色生活环境经过长久的历史积淀,成为满族人生产劳作的要素,白色也逐渐抽象为和平生活的象征符号。白色背后深蕴的社会心理是满族人对和平生活的追求与向往。白色成为平安稳定的生息地的象征。
满族曾长期处于民族迁徙、战争之中。合并各部落、四处征战的状态使许多满族人内心痛苦、紧张,生活困顿、凄惨。“沙漠万里程,安得善水草。长嘶西北风,筋力不奈老。”“胡笳曲就声多怨,破镜诗成竟自惭。”[8](5)“惊风随壑转,残雪扑鞍飞。战地人烟少,颓垣雉兔肥。”[8](17)征战流血是痛苦的回忆,因此满族人尚白贱红,把红色作为丧事时使用的颜色。在满族人看来,红色预示着血光之灾,意味着流血牺牲。“日暮荒祠,泪下如雨。饥食草根,草根春不生。单衣曝背,雨雪少晴……杀戮流血,祸及鸡狗。日凄凄,风破肘。流民掩泣,主人摇手。”[8](1)满族尚白的艺术形式表现了满族人追求和平、向往幸福的生活观念,每一个满族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结束动荡血腥的征战生活。
满族入关后,随着民族杂居,满族受汉俗的影响,尚白习俗逐渐减弱。《燕京岁时记》记载:“惟内廷及宗室王公等例用白纸、缘以红边、蓝边。”满族喜爱的颜色开始和满族八旗所属颜色相关。晚清以后,满族人沿袭汉俗,开始喜红丧白。启功先生在《古诗四十首》之六中写过满族尚白习俗的转变:“长白雪长白,皓洁迎新年。神板白‘挂钱’,门户白春联。地移习亦变,喜色朱红鲜。筋力自此缓,万事俱唐捐。”[9](242)历史生境使得满族的审美习俗有了改变,时至今日,满族喜爱的颜色越来越丰富。
参考文献:
[1](元)脱脱,等,撰.金史·卷一○七[M].张彦博,崔文辉,标点.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2](宋)宇文懋昭,撰.大金国志[M].崔文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1986.
[3]王纯信,黄千,主编.满族民间剪纸[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9.
[4][美]C.S.霍尔,等.荣格心理学入门[M].冯川,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
[5]王宏刚.满族与萨满教[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2.
[6]杨英杰.清代满族风俗史[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7]谷长春,主编.满族口头遗产传统说部丛书——萨布素将军传[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8](清)杨钟羲,撰集.雪桥诗话续集[M].刘承干,参校.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
[9]启功.启功丛稿[M].北京:中华书局,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