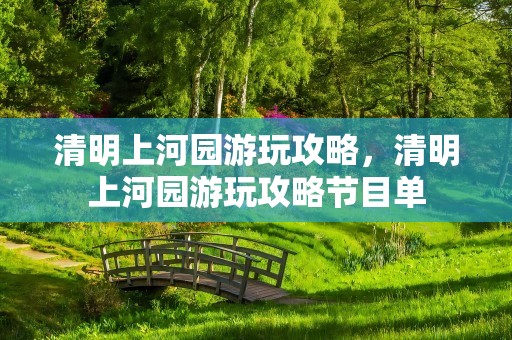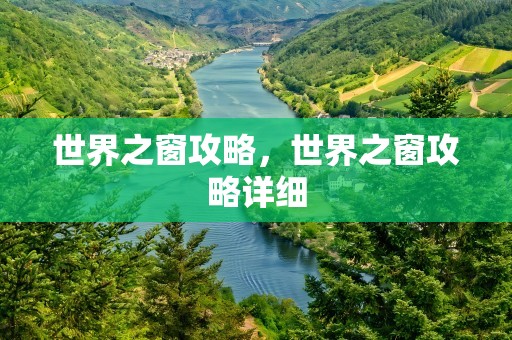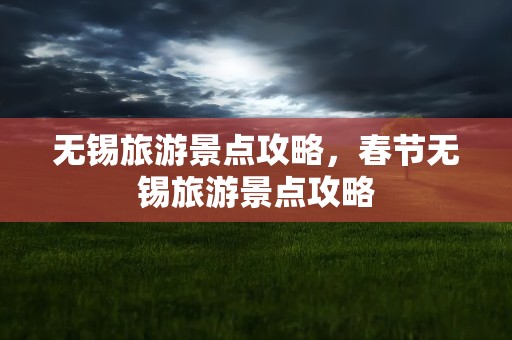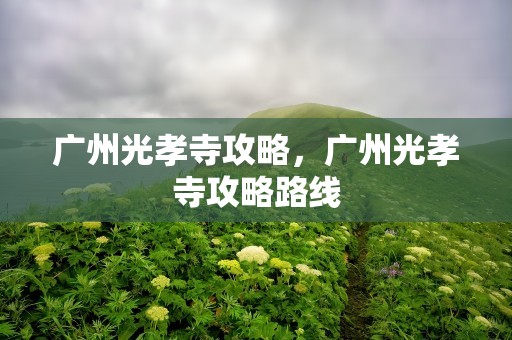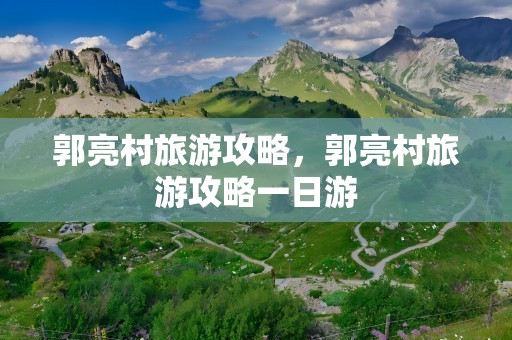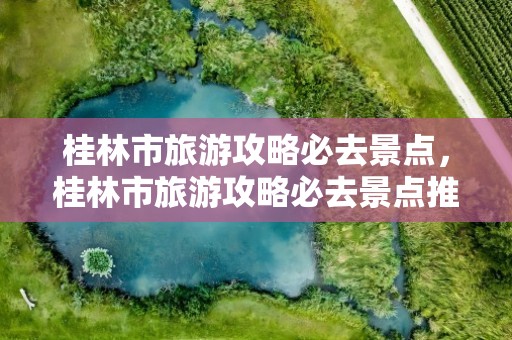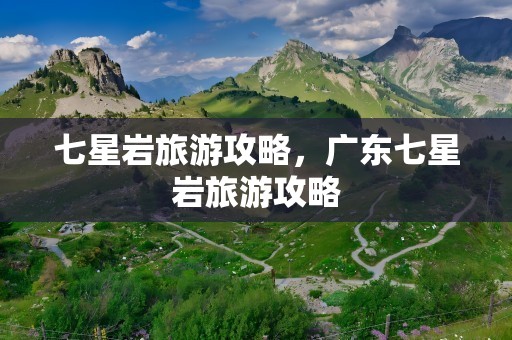在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大军先后向欧洲发动数次大规模的西征,几乎战无不胜。在这几次西征中,蒙古军队数量通常较少,总数最多不过20万人(在欧洲战场从未超过15万),在单次战役中的人数则更少,没有再现昔日蒙古大军攻打金国钧州一战中“层层叠叠,厚20里”的列阵,然而却屡战屡胜。这是什么原因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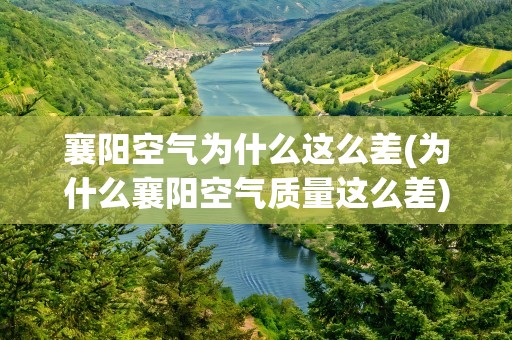
天生就是斗士
和中国北方的其他游牧民族一样,蒙古人从小就是斗士,在马背上长大,小时候的玩具就是弓箭,成年后就早可以算成是职业军人。由于他们在严寒和艰苦的环境中长大,具有极为坚韧耐劳的性格,对物质条件的待遇几乎从不讲究,这使蒙古军队的后勤负担显得很轻。他们的连续作战的意志和能力,更使西方那些养尊处优的贵族骑兵们难以望其项背。
蒙古人的社会组织也与战争非常适应,各部落的首领既是生活生产的管理组织者,又是军事行动的管理组织者。在对外发动战争时,可以全民动员,不分男女老幼全部参加作战行动。如对花剌子模国的长期围困,就是全民参与,在城下放牧生活,维持着军队持续不断的攻击力,直到城市被攻克。
未必劣等的蒙古马
如果用现代人的眼光看,蒙古马应该算作是世界上最劣等的马。这种马不仅身材矮小、跑速慢,而且越障碍的能力也远远不及欧洲的高头大马。但是,蒙古马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的马,对环境和食物的要求也是最低的。无论是在亚洲的高寒荒漠,还是在欧洲的辽阔平原,蒙古马随时都可以找到食物。可以说,蒙古马具有最强的适应能力。它们可以长距离不停顿地奔跑,无论严寒酷暑都可以在野外生存。同时,蒙古马可以随时胜任骑乘和拉车载重的任务,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好马最终全部被蒙古马取代的原因。
除了作为骑乘工具外,蒙古马还是一种食物来源——蒙古骑兵使用大量的母马,可以提供马奶,这也减少了蒙古军队对后勤的要求。
蒙古马的这种特殊优势,使得蒙古军队具有了在当时任何军队都难以比拟的速度和机动能力。比如,在1241年冬季,蒙古将军速不台的主力骑兵仅仅只用了3天的时间,就从鲁斯卡山口越过喀尔巴阡山脉,突然出现在多瑙河流域的格兰城下,而两地之间的距离竟有300多公里之遥,布满积雪,且多是无路的山地。
攻无不克的武器
蒙古人所使用的抛石车、火箭等中原新式武器,原是中原各国在守备坚固的城防时,用于抵御蒙古军队的武器。公元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就曾将在开封等地虏获的工匠、作坊和火器全部掠走,还把金军中的火药工匠和火器手编入了蒙古军队。次年,蒙古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西征,新编入蒙军的火器部队也随军远征。
火药和火箭类武器出现在冷兵器时代,其威力自然是惊人的,另外,对于从未见过它们的敌人来说,也有巨大的心理震慑作用。当时的波兰人描绘蒙古人从一种木筒中成束地发射火箭,因为木筒上绘有龙头,因此被波兰人称作“中国喷火龙”。在欧洲战场上,很多时候火药类武器对城墙尚未造成完全破坏时,守军便会失去战斗的意志,开始弃城逃亡。
蒙古人还拥有当时射程最远、杀伤力最大的组合式弓。这种武器通常由后背上的一条动物筋、弓肚上的一层角质物和中间的一个木架组成。这种弓的拉力在50公斤和75公斤之间,又很短小便于骑兵运用自如。这种弓射出的箭杀伤范围可达300米,如果在箭上装备上锋利的金属箭头,便能穿透最厚的盔甲。这种强劲的武器配合蒙古骑兵的机动力,使得蒙古人得以纵横欧亚,无人能挡。
蒙古人极其擅长被古罗马人称为“安息人射箭法”的战法,即一边逃走,一边向后方的敌人射箭。(蒙古人称这种战法为“曼古歹”)。这种战术的精髓在于:一从远距离攻击敌人,二持续不断地攻击敌人,三不给敌人还手的机会。在这种攻击下,不论敌人的精神和装甲多么坚强,彻底崩溃只是时间的问题。当时欧洲骑士大多配备重盔重甲,虽然近战时十分强大,机动力却根本无法和蒙古骑兵相比。如果碰上蒙古骑射手,不仅追不上,连逃都逃不掉,只有作箭靶子的份。而且蒙古骑兵不像欧洲骑士那样完全依赖强攻,他们往往当先用弓箭把敌人杀伤大半然后才与敌人短兵相接。1241年4月,蒙古骑兵就靠这种战法在多瑙河畔大破欧洲最精锐的10万匈牙利大军(由匈牙利国王贝拉四世率领),杀敌7万余,用弓和箭演奏了一曲“红色多瑙河”,几乎彻底消灭了欧洲的抵抗力量。
欧洲方阵的克星
事实上,蒙古军队的轻骑兵在任何时候都无法一对一地战胜欧洲的重装甲骑兵,欧洲重装甲骑兵的长矛和重剑杀伤力远大于蒙古骑兵手中的马刀、长矛或狼牙棒。欧洲骑兵的马也远比蒙古马高大。在战场上,欧洲重装甲骑兵往往结成整齐的方阵,如同铁壁铜墙一般势不可挡。但蒙古骑兵的战略战术恰恰是欧洲方阵的克星。
欧洲军队有惯常的骑士之风,崇信正面一对一的堂堂正正的战斗。可惜蒙古人并不按照欧洲骑士的规矩来。他们特别强调部队的机动胜,以远距离的包抄迂回、分进合击为主要战术特征。蒙古人的远距离机动达到了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程度,他们常常可以上百里地大规模机动,使敌人很难预料和防范到他们的攻击。
蒙古人在战斗中亦很少依赖单纯的正面冲击,通常使用的方法是,一小部分骑兵不停地骚扰敌军,受攻击后撤退。而遭到攻击的西方军队无论是步兵方阵还是骑兵方阵此时都很难迅速回击,因为他们必须保持队形的严密向前推进,否则无法利用自己的优势杀伤蒙古兵。通常蒙古军队的骑兵只要进行一两次这种冲击就会让敌军军心动摇、队形混乱。一但敌军开始后撤,宽大的蒙古骑兵队形就会迅速变成包抄队形,对敌军进行近距离的砍杀。
正是凭借着高度的机动性和灵活性,蒙古大军在欧洲消灭了大量装甲坚固但行动笨拙的欧洲军队。由于欧洲军队在速度上的劣势,使得从战场上逃回来的人极少,以至很久以来,欧洲人始终认为蒙古军队靠数量庞大而取胜。欧洲军队主要依赖近距离的格斗杀伤,使得蒙古军队在运用机动作战时,只有少量的伤亡。现代的欧洲军事史学专家认为,欧洲军队和蒙古军队在战争中的伤亡比例,也许是冷兵器时代最为悬殊的。
综上分析,蒙古国军队在亚欧大陆东征西讨所向无敌,几乎就是必然的结果。而在日本和越南战场上的失败,恰好是因为这两个战场是蒙古军队根本无法发挥优势的地方。他们必须下马乘船,靠老天保佑才能平安到达目的地。而抵岸后,在丛林山地面前,他们无法大规模地穿插机动,甚至还不能骑马。更为糟糕的是,潮湿的空气使他们难以适应,成为病夫,或者被瘟疫夺去了生命,就像欧洲军队不能适应他们一样。
这个问题问得不对。
并不是古代能人“都”喜欢隐居深山,只是一部分能人喜欢这么做。不然的话,就不会有“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世,大隐隐于朝。”这句古话了。
题目中的古代能人,就是这句古话中的“隐”,也称隐士,用当今白话来说,就是隐居起来研究某种学问的人。
你要隐,首先得是“士”,也就是知识分子。所以住在深山的农民樵夫和猎人,并不算隐士或能人。
深山无论对于古代人还是现代人,都具有很强的诱惑力。高山流水、树木苍翠、万籁俱静惟泉水淙淙,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饱览群书亦或是身怀绝技的人,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惊艳,深山因此成了他们眼中的世外桃源。
古往今来,有能力的人,总热衷于找寻一处别具一格的居住地。环境优美、隔绝世俗喧嚣的深山,自然是首选。住在这样的地方,高兴了采桑作画,郁闷了独酌赋诗,千古名篇,就在日常的喜乐愤郁中诞生。
从常人的印象来说,古代的能人隐士,通常具有如下品质: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超凡才德学识、不愿入仕。
比如众所周知的有鬼谷子、颜回、竹林七贤,更有尧舜时代的“三代宗师”许由。传说尧帝要把君位让给他,他推辞不受,逃于箕山下,农耕而食;尧帝又让他做九州长官,他到颍水边洗耳,表示不愿听到这些世俗浊言。于是后世就把许由和与他同时代的隐士巢父,并称为巢由或巢许,用以指代隐居不仕者。
他们可以说是真正看破生死红尘,以天地为家的与世无争之人,所以能在深山隐居不出。
但还有一种能人,他们之所以隐居深山,只是因为暂时无人赏识,无法入仕,便以避世为名隐遁山林,等待伯乐的发掘。像姜太公、诸葛亮、李白、严子陵等,都是隐于朝野外,却一直在等待独具慧眼的君主们发掘自己的“能人”。
这两类人,是隐居深山的主要群体。
湖北襄阳空气质量良好。
襄阳市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这里既有滔滔汉水流经,又有干冷、暖湿空气交绥,冬寒夏暑,冬干夏雨,雨热同期,四季分明,加之复杂多样的地貌类型对气候要素产生明显的再分配作用,使得市内气候形成了各种类型。
境内繁多的植物、动物种类,即受惠于气候的复杂多样性,全市年平均气温除高山以外,一般均在15~16℃之间,1月2~3℃,2月15~16℃,7月27~28℃,10月16~17℃,所以空气质量很好。
湖北襄阳简介
襄阳市,曾用名襄樊,湖北省辖地级市,地处中国华中地区、湖北西北部,汉江中游,地跨东经110°45′—113°06′、北纬31°13′—32°37′;属亚热带季风气候;全市共辖3个市辖区、3个县,代管3个县级市,总面积1.97万平方千米,截至2022年,常住人口527.6万人。
襄阳位于长江支流汉江的中游,是鄂、豫、渝、陕毗邻地区的中心城市,襄阳市的发展肇始于周宣王封仲山甫(樊穆仲)于此,从荆州牧刘表徙治襄阳始襄阳历来为府、道、州、路、县治所,襄阳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以上内容参考:百度百科—襄阳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