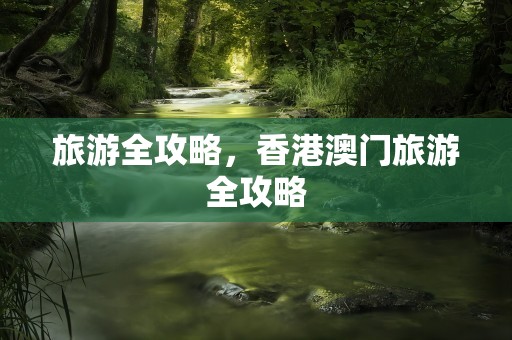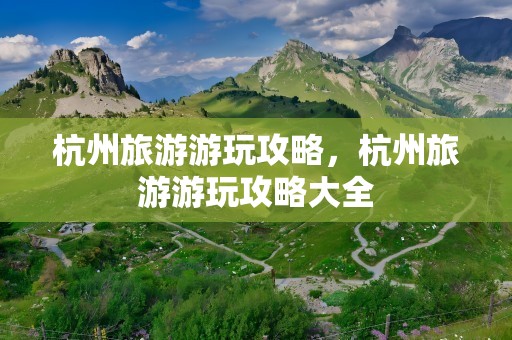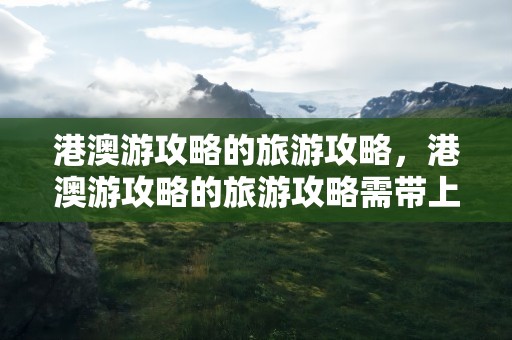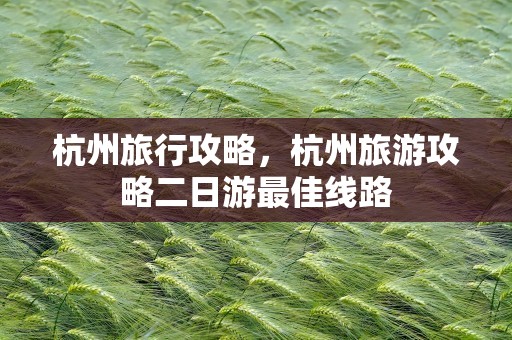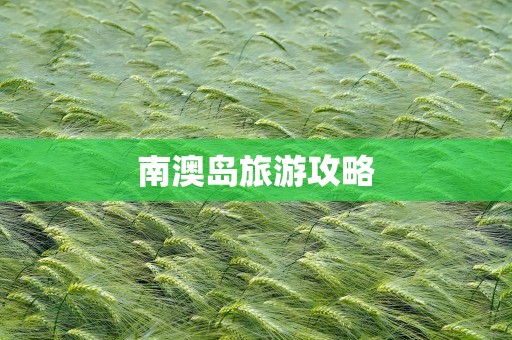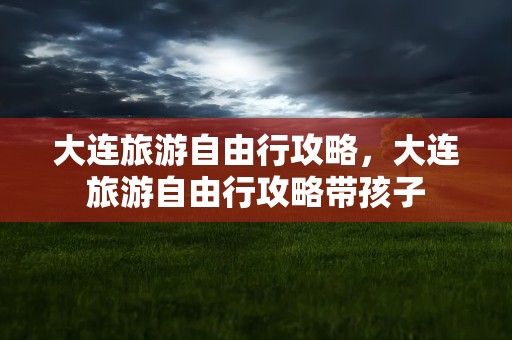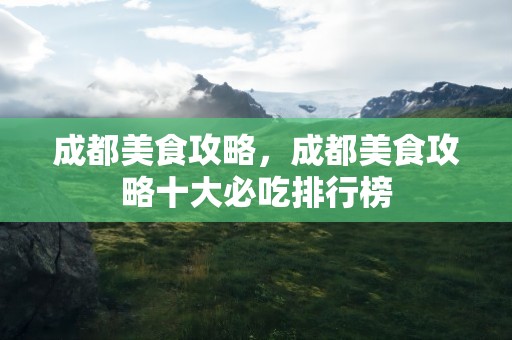南极被称为世界的第七大陆。是地球上最后被发现,唯一没有人员定居的陆地

南极冰川
其原因就是因为南极恶劣的气候条件,让人望而止步。南极洲腹地几乎是一片不毛之地。那里仅有的生物就是一些简单的植物和一两种昆虫。植物难于生长,偶尔能见到一些苔藓、地衣等植物。
南极大陆还是最难接近的大陆。与南极大陆最接近的大陆是南美洲,它们之间是970千米宽的德雷克海峡。南极大陆与其他大陆不仅相距遥远,而且周围还被数公里乃至数百公里的冰架和浮冰所环绕,冬天时浮冰的面积可达1900万平方千米;即使在南极的夏天,其面积也有260万平方千米;南极大陆周围海洋中还漂浮着数以万计的巨大的冰山,为海上航行造成了极大的困难和危险
所以列强不会冒着如此多的危险去抢占一块对他们毫无用处的土地
1.新西兰没有蛇,是真的吗?
对于生活在北半球的人来说,蛇在生活中是非常常见的,但是在新西兰这个被称之为羊的国度里,却很难见到蛇的踪迹。因此,人们普遍认为新西兰没有蛇这个说法是真的。
2.为什么新西兰没有蛇?
为什么新西兰没有蛇呢?据研究,这主要是因为新西兰地处偏远,较为孤立,导致动植物的迁移变得困难。而蛇也是由陆地迁移到岛屿上的,因此新西兰的蛇类物种相对较少,乃至于没有蛇的存在。
3.新西兰没有蛇的好处
新西兰之所以能够保持没有蛇的状态,是因为人们非常重视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没有蛇的存在,维护了新西兰独特的生态系统,使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环境有着天壤之别。这也是新西兰成为生态旅游胜地的原因之一。
4.新西兰是否存在蛇
虽然新西兰一般被认为是没有蛇的国家,但是一些人仍然声称看到过蛇的存在。这些所谓的蛇都是外来物种,可能是因为人类携带进入了新西兰。新西兰政府一直在努力打击外来物种的入侵,以保护当地的生态环境。
5.新西兰对待蛇的态度
尽管新西兰没有蛇,但是当地人对待蛇的态度依然注意。他们非常看重对狗进行管教,以免其走失时对野生生物造成伤害。此外,当地人也认为,若是有人在新西兰放生蛇类物种,那么这个人将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6.新西兰没有蛇的可能影响
新西兰没有蛇的状态对于当地生态环境而言,是件好事。然而,由于当地生态系统独特性的存在,蛇类物种如果被带入新西兰,将会对其造成极大的威胁。
7.怎么保持新西兰没有蛇的环境
需要注意的是,为保持新西兰没有蛇的独特生态,我们也需要注意不带入外来蛇类物种。因此,当前旅游业者、海员和园艺工人都需要承认和履行其责任,以防止外来物种和无意中伴随而来的植物害虫入侵。这样才能有效地维护新西兰的生态环境。
8.新西兰没有蛇的神话传说
在马奥里文化中,蛇是一种圣洁的动物,代表着健康和繁荣。在马奥里文化中,蛇的形象通常出现在食品、衣物和艺术品中。而早期新西兰毛利人则从未见到过蛇,因此在毛利文化中,蛇被认为是一种神话传说,它代表着荒凉和危险。这也影响了当地人对于蛇的态度.
不归作:论顾城之死
继海子卧轨自杀后,朦胧派代表诗人顾城亦于新西兰一孤岛自缢身亡,国内闻之哗然,智者仁者,见仁见智,喧嚣一时。然——“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骚客风流,名士清誉,而今安在哉!
我于顾城生平及死因,未能悉知,几本悼念追怀的小书,随手翻阅,过则忘之;即其诗集、《英儿》等,也未曾细读——我不是顾城亲友,顾城亦非我知己,当其激扬文字、笑傲湖山之时,他根本不知世上还有我等野氓“存在”!——然,今夜,月凉似水,树影同藻,偶有狗吠深巷中,若有所思,若有所悟,顾城,黑夜曾给你一双黑色的眼睛,你用来发现今夜在你坟墓之上持续隆起的光明了吗?
我相信那些焚烧自己诗集的诗人所说的话,更景仰那些靠死亡来证实的生命,敲着欲凝成冰的寒气,独自蜷缩在乱山深处的一间茅屋里,我想刻下死者的声音,想沿着时光的隧道走进生命的本质存在中。今夜,我把你完全奉献出来,引导那颗星走进大地的胸腔去吧!
死的底层到底隐藏着什么?莫非也如月亮的背面一样荒凉,我们不幸生于一个不再需要死亡的时代,一个连最后的黑夜都不能赢得尊重的时代,一个连彻底的沉默都会带来耻辱与诽谤的时代,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唯一对我们还怀有怜悯之情的诗神在森林之外却遭到傲慢者的无端杀戮,而不能再对我们有所救助;甚至还不能将其绝望的呻吟传递出来,她在忍受着怎样的不可言说的苦痛呀!
随便翻开一本诗集,就会发现,诗人的生命多从喜剧开始,以悲剧结束。因此,叔本华在《读书》一文中早就希望有人撰写一部悲剧性的历史:“他要在其中描述,世界上许多国家,无不以其大文豪及大艺术家为荣,但在他们生前,却遭到虐待;他要在其中描写,在一切时代和所有的国家中,真和善常对着邪和恶做无穷的斗争;他要描写,在任何艺术中,人类的大导师几乎全部遭灾殉难;他要描写,除了极少数人外,他们从未被赏识和关心,反而常受压迫,或流离颠沛,或贫寒饥苦,而荣华富贵则为少数碌碌无为者所享受,他们的情形和《创世纪》中的以扫相似。”(旧约故事:以扫与雅各为孪生兄弟,在其外出为父亲击毙野兽时,雅各却穿上兄长的衣服,在家里接受父亲的祝福。)
——还记得我们共同的祖先屈原吗?
公元前二百七十八年夏历五月五日,屈原自投于汨罗江。《史记·屈原列传》:“屈平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以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固《离骚赞序》:“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在野又作《九章赋》以讽谏,卒不见纳,不忍浊世,自投汨罗。其辞为众贤所悼悲。”王逸《九歌序》:“屈原放逐,窜伏其域,怀忧苦毒,愁思沸郁。出见俗人,祭祀之礼,歌舞之乐,其辞鄙陋,因为作《九歌》之曲,章句杂错,而广异义焉。”又《天问序》:“《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林,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太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又《离骚经序》:“屈原放在草野,复作《九章》,援天引圣,以自证明,终不见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浊世,遂赴汨渊自沉而死。”
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平则鸣。……尤择善鸣者而假之鸣。”有此一鸣,汉文化揭开了辉煌的一页,屈原,亦西方之唯吉尔,且其遇其思过之。
屈原诗中很多地方谈到死。《离骚》首言岁月流逝,壮志难酬之恨,“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又言惟愿建立功名,不惮死亡,“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终遭谗放逐,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奈荃不察其忠诚,信谗斋怒,“虽九死其犹未悔”,“伏洁白以死直”,长诗最后,慨然叹息,“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彭咸,据王逸注:“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
《国殇》最末一句:“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怀沙》:“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忆往昔》:“焉舒情而抽信兮,怅死亡而无聊。”“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悲回风》:“宁溘死而流亡兮,不忍为此常愁。”《天问》:“何所不死,长人何守?”(长人,一说为长寿之人)“延年不死,寿何所止。”“天式纵横,阳离爱死。”《渔父》:“宁赴湘流,葬于江鱼腹中。”
《荀子·礼论》:“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论语·先进》:“未知生,焉知死。”以孔子之见,死可以行之而不能言之;而屈原,不仅怀必死之志,而且对死亡本身也进行过哲学思考。其所以投江,前人所论颇多,约略言之:屈原出自楚国世家,既具内美,又重修能,二十五岁即参与朝政,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官至左徒。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本可有所作为。当时天下情势,不归于秦,即归于楚,战国七雄,惟楚能与秦抗衡。然楚怀王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原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兵败蓝田,亡其六郡,身客死于秦,为天下笑。屈原也自左徒降为三闾大夫。顷襄王即位,贬逐江南荒远之地。“楚国大夫憔悴日,应寻此路到潇湘。”这是杜牧游行兰溪时写下的诗句(《全唐诗》卷五二二),每一读之,令人怆然。政治上的失意,爱情上的沉郁,对家国前途的焦虑,对民生苦艰的悲戚,逐绪而来。他居庙堂之高则忧其君,处江湖之远则忧其民,是近亦忧,退亦忧,既不能与民同乐,独乐何益!他的慨然就死,是对黑暗现实、贫乏时代的抗争。这与陶渊明“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饮酒》十一)是有些区别的。
屈原一身兼有政治家与诗人两重品性,而后者无疑是主要的。他既非伊尹、吕望细大不捐、强力忍垢之辈,亦非曹操、桓温之流的奸雄,更以苏秦、张仪等凭三寸不烂之舌搏取富贵为耻,且不屑与子兰、上官、郑袖等周旋,可以说,他政治上的报复在任何时代都不可能实现,因此,他更是一位诗人。高洁自许,目下无尘,纫兰制荷,养菊栽蕙,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文选》卷五十三载李康《运命论》),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这也是势使之然。处在战国时代,鸡鸣狗盗之徒,亦可拖青纡紫;翻云覆雨之辈,偏能乘车挂印;就是下流到吮疮舔痔者,犹能载千金以归,可以说,士无贤不肖,均有用之才,独诗人无补于世。故同时其他诸国,传诗甚少。惟屈原举世混浊而独清,众人皆醉而独醒,被发行吟,阳狂泽畔。《离骚》:“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兮故都?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无人知之,是其一;不与美政,是其二;这应该是屈原涉江怀沙的主要原因。
屈原对死亡的思考在当时也有其代表性:首先,他意识到“人固有一死”,这个尽头是谁也不能避免的,恐惧要不的,要正视这个冰冷的深渊;其次,他是怀着“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心情离开人世的,即使再给予他新的生命,他也不可能有别的选择,因为他对自己不苟流俗,对美好理想,上下求索,持之以恒,以至于死的一生,并无悔恨,他甚至对死亡还进行了美学层面上的思考,他的确作到了“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唯一能够引起他的担忧的也许是“身死亡而道不用”,未来世纪倾听不到或理解不了他悲愤至极的言说。他的诗乃发愤而作,慨天道不公,不佑善人,亦司马迁《伯夷列传》之意。他在诗中灌注的是真实的自我,灌注的是只有真实生命才会具有的倔强的不息的激流,想象奇瑰,千回百曲,上则共日月争辉,下则与河山表里,论其对人类心灵的冲击力,千百年来,罕能继武。
宋太祖尝言:“使李煜以作诗工夫治国,岂为吾虏也!”李煜国破身囚,终日以泪洗面,因怀故土,竟被毒死,然“词经”铸就,不知多少“潇湘妃子”为之垂泪,问陈桥兵驿,赵氏陵阙,而今安在哉!国君李煜之不幸,正词人李煜之幸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果何为哉!”(王国维《人间词话》)
清代学者费锡璜《汉诗总说》云:“屈原将投汨罗而作《离骚》,李陵降胡不归而赋别诸诗,蔡琰被掠失身而赋《悲愤》诸诗,千古绝调,必成于失意不可解之时。惟其失意不可解,而发言乃绝千古。下此则嵇康临终,杜甫遭乱,李白投荒,皆能响继前贤。外此则吾未之见也。”
屈赋的风格兼有《诗经》之风雅,与《庄子》之“怒而飞”相近,而其精神,又渊出孔子,虽取镕经意,亦自铸伟辞,他是先秦歌诗之集大成者,故能气往铄古,词来切今,其衣被辞人,非惟一代。李白长篇歌行与其风神一脉相承,而杜甫则是他精魂之重塑者。——笔者也认为他生得其时(汉民族历史上的第一个贫乏时代),死得其所,故作《相见欢》以咏之:
西风惊梦船窗。蓼兰香。记著落花时节去潇湘。
天已问。魂何恨。碧波伤。遗下高山贤哲几番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