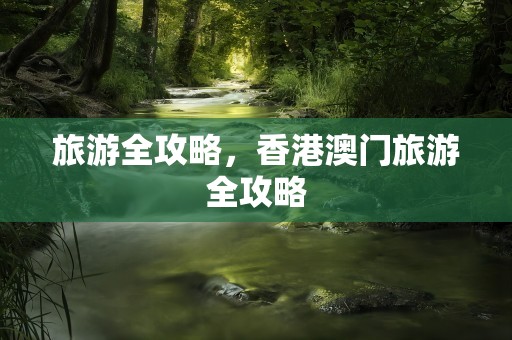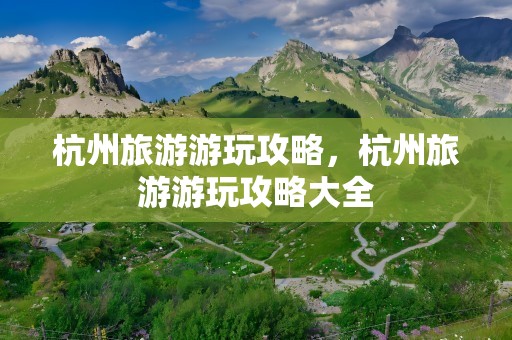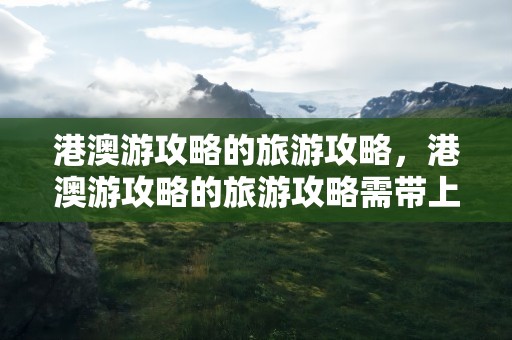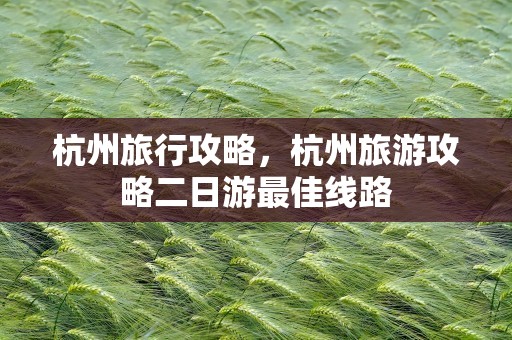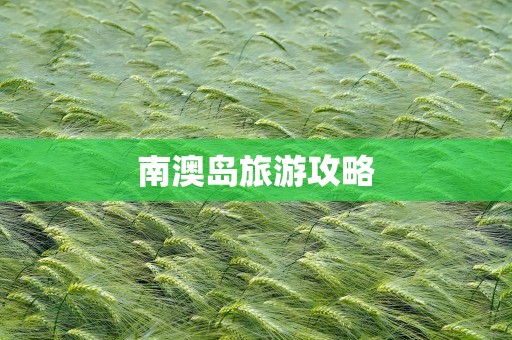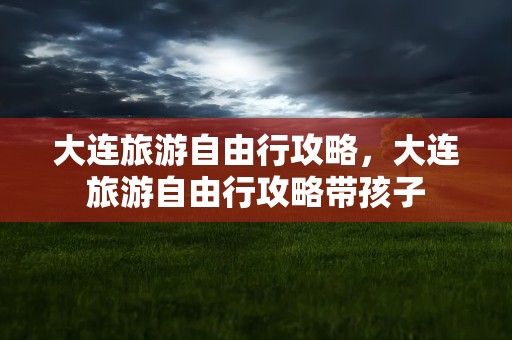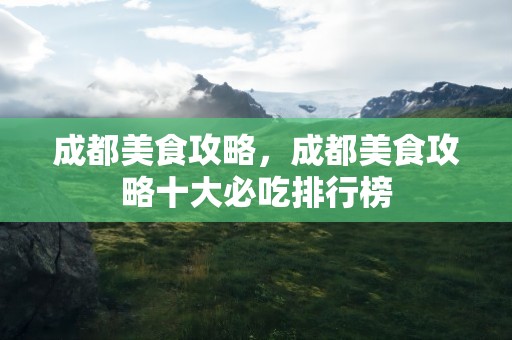大家知道,那闪烁着珠光宝气的珍珠,是在蚌体中生长的。河蚌这种浮游生物,从古代开始,已经盛产在淮河南岸的河滩,并且成为一道自然风景线。每逢淮水退落,河滩上常常是一片银光闪烁的蚌壳,古人在这定氦翅教俨寄愁犀传篓里采蚌取珠,成为当地风俗。所以从凤阳长淮卫到这里的淮河南岸,还有“珍珠滩”的美称。上个世纪80年代初,蚌埠西郊地表出土的河蚌化石,贝壳岩层,经古生物学家鉴定,它就是可以培育珍珠的“丽蚌”,与两千多年前的《尚书.禹贡》记载的“淮夷宾珠”相互印证,充分说明了当年这里就是盛产河蚌的“古采珠之地”。

今天所在的蚌埠,北宋时期曾是淮河岸边的一个渔村渡口。这个停泊船只的埠头,接待着南北过往的行人渡过淮河,每遇风浪又供人们住下歇脚。因此,南宋时期人们就是把这里叫着“蚌埠店”。明代被划归凤阳府,为“蚌埠集”。从凤阳到怀远一条官道经过龙子河,有座小石桥旁,水中也有许多河蚌,人们聚集这里采蚌取珠,于是把桥也叫着“珍珠桥”。蚌埠集以南有座小山下,那时侯,每当阳光照耀,地上蚌壳银光闪闪,因此,人们也就把这座山称为“蚌山”。今天,它已经成为蚌埠城市的一个区名。上个世纪70年代,西哈努克亲王从北京到上海访问,经过这里向翻译问到:“蚌埠是什么地方?翻译妙语答:珍珠城”。。从此,“珠城——蚌埠”的美称传遍全国。
雨点瞄着每株青草落下来,因为风吹的原因,它落在别的草上。别的雨点又落在别的草上。春雨落在什么东西都没生长的、傻傻的土地上,土地开始复苏,想起了去年的事情。雨水排着燕子的队形,以燕子的轻盈钻入大地。这时候,还听不到沙沙的声响,树叶太小,演奏不出沙沙的音乐。春雨是今年第一次下,边下边回忆。有些地方下过了,有些地方还干着。春雨扯动风的透明的帆,把雨水洒到它应该去的一切地方。
春雨继续下起来,无需雷声滚滚,也照样下,春雨不搞这些排场。它下雨便下雨,不来浓云密布那一套,那都是夏天搞的事情。春雨非不能也,而不为也。打雷谁不会?打雷干吗?春雨静静地、细密地、清凉地、疏落地、晶亮地、飘洒地下着,下着。不大也不小,它们趴在玻璃上往屋里看,看屋里需不需要雨水,看到人或坐或卧,过着他们称之为生活的日子。春雨的水珠看到屋子里没有水,也没有花朵和青草。
春雨飘落的时候伴随歌声,合唱,小调式乐曲,6/8拍子,类似塔吉克音乐。可惜人耳听不到。春雨的歌声低于20赫兹。旋律有如《霍夫曼的故事》里的“船歌”,连贯的旋律拆开重新缝在一起,走两步就有一个起始句。开始,发展下去,终结又可以开始。船歌是拿波里船夫唱的情歌小调,荡漾,节奏一直在荡漾。这些船夫上岸后不会走路了,因为大地不荡漾。春雨早就明白这些,这不算啥。春雨时疾时徐、或快或慢地在空气里荡漾。它并不着急落地。那么早落地干吗?不如按6/8的节奏荡漾。塔吉克人没见过海,但也懂得在歌声里荡漾。6/8不是给腿的节奏,节奏在腰上。欲进又退,忽而转身,说的不是腿,而是腰。腰的动作表现在肩上。如果舞者头戴黑羔皮帽子,上唇留着浓黑带尖的胡子就更好了。
春雨忽然下起来,青草和花都不意外,但人意外。他们慌张奔跑,在屋檐和树下避雨。雨持续下着,直到人们从屋檐和树底下走出。雨很想洗刷这些人,让他们像桃花一样绯红,或像杏花一样明亮。雨打在人的衣服上,渗入纺织物变得沉重,脸色却不像桃花那样鲜艳而单薄。他们的脸上爬满了水珠,这与趴在玻璃上往屋里看的水珠是同伙。水珠温柔地俯在人的脸上,想为他们取暖却取到了他们的脸。这些脸啊,比树木更加坚硬。脸上隐藏与泄露着人生的所有消息。雨水摸摸他们的鼻梁,摸摸他们的面颊,他们的眼睛不让摸,眯着。这些人慌乱奔走,像从山顶滚下的石块,奔向四方。
春雨拍打行人的肩头和后背,他们挥动胳膊时双手抓到了雨。雨最想洗一洗人的眼睛,让他们看一看——桃花开了。一棵接一棵的桃树站立路边,枝桠相接,举起繁密的桃花。桃花在雨水里依然盛开,有一些湿红。有的花瓣落在泥里,如撕碎的信笺。如琴弦一般的青草在桃树下齐齐探出头,像儿童长得很快的头发。你们看到鸟儿多了吗?它们在枝头大叫,让雨下大或立刻停下来。如果行人脚下踩上了泥巴应该高兴,这是春天到来的证据。冻土竟然变得泥泞,就像所有的树都打了骨朵。不开花的杨树也打了骨朵。鸟儿满世界大喊的话语你听到了吗?春天,春天,鸟儿天天说这两句话。
雨落入大海之后不再想念陆地
我终于明白,水化为雨是为了投身大海。水有水的愿景,最自由的领地莫过于海。雨落海里,才伸手就有海的千万只手抓住它,一起荡漾。谁说荡漾不是自由?自由正在随波逐流,“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雨在海里见到了无边的兄弟姐妹,它们被称为海水,可以绿、可以蓝、可以灰,夜晚变成半透明的琉璃黑。雨落进海里就开始周游世界的旅程,从不担心干涸。
我在泰国南部皮皮岛潜泳,才知道海底有比陆上更美的景物。红色如盆景的珊瑚遍地都是,白珊瑚像不透明的冰糖。绚丽的热带鱼游来游去,一鱼眼神天真,一鱼唇如梦露。它们幼稚地、梦幻地游动,并不问自己往哪里游,就像鸟也不知自己往哪儿飞。
人到了海底却成了怪物,胳膊腿儿太长,没有美丽的鳞而只有裤衩,脑袋戴着泳镜和长鼻子呼吸器。可怜的鱼和贝类以为人就长这德性,这真是误会。我巴不得卸下呼吸器给它们展示嘴脸,但不行,还没修练到那个份儿上,还得呼吸压缩氧气,还没掌握用鳃分解水里氧气的要领。海底美啊,比九寨沟和西湖都美。假如我有机会当上一个军阀,就把军阀府邸修在海底,找我办事的人要穿潜水服游过来。海里的细砂雪白柔软,海葵像花儿摇摆,连章鱼也把自己开成了一朵花。
上帝造海底之时分外用心,发挥了美术家全部的匠心。石头、草、贝壳和鱼的色彩都那么鲜明,像鹦鹉满天飞。上帝造人为什么留一手,没让人像鸟和鱼那么漂亮?人,无论黄人、黑人、白人,色调都挺闷,除了眼睛和须发,其余的皮肤都是单色,要靠衣服胡穿乱戴,表示自己不单调。海里一片斑斓,看来上帝造海底世界的时候,手边的色彩富裕。
雨水跳进海里游泳,它们没有淹死的恐惧。雨水最怕落在黄土高坡,“啪”,一半蒸发,一半被土吸走,雨就是这么死的,就义。雨在海里见到城墙般的巨浪,它不知道水还可以造出城墙,转瞬垮塌,变成浪的雕堡、浪的山峰。雨点从浪尖往下看,谷底深不可测,雨冲下去依然是水。浪用怀抱兜着所有的水,摔不死也砸不扁。雨在浪里东奔西走,四海为家。
雨在云里遨游时,往下看海如万顷碧玉,它不知那是海,但不是树也不是土。雨接近了海,感受到透明的风的拨弄。风把雨混和编队,像撒黄豆一样撒进海里。海的脸溅出一层麻子,被风抚平。海鸥在浪尖叼着鱼飞,涛冲到最高,卷起纷乱的白边。俯瞰海,看不清它的图案。大海没有耐心把一张画画完,画一半就抹去另画,象形的图案转为抽象的图案。雨钻进海里,舒服啊。海水清凉,雨抱着鲸鱼的身体潜入海水最深处,鱼群的腹侧如闪闪的刀光,海草头发飞旋似女巫。往上看,太阳融化了,像蛋黄摊在海的外层,晃晃悠悠。海里不需要视力,不需要躲藏。雨水落大海之后不再想念陆地。
树用每一片叶子承接雨
大雨把石子路面砸得啪啪响。进森林里,这声音变成细密的沙沙声。树用每一片叶子承接雨水,水从叶子流向细枝和粗枝,顺树干淌入地面。地面晃动树根似的溪流,匆忙拐弯、汇合,藏进低洼的草丛。
雷声不那么响亮,树叶吸收了它的咳嗽声,闪电只露半截,另一半被树的身影遮挡。我想起一个警告,说树招引雷击,招雷的往往是孤零零的树,而不是整个森林。对森林里的树来说,雷太少了。
雨下得更大,森林之外的草坪仿佛罩上白雾,雨打树叶的声音却变小,大片的水从树干流下来,水在黑色的树干上闪光。
我站在林地,听雨水一串串落在帽子上。我索性脱下衣服,在树叶滤过的雨水里洗澡,然后洗衣服,拧干穿上。衣服很快又湿了。雨更大的时候,我在衣兜里摸到了水,早知道这样,往兜里放一条小金鱼都好。
后来,树叶们兜不住水,树木间拉起一道白色的雨雾。我觉得树木开始走动。好多树在雨中穿行。它们低着头,打着树冠的伞。
小鸟此时在哪儿呢?每天早晨,我在离森林四五百米的房子里听到鸟儿们发出喧嚣的鸣唱,每只鸟都想用高音压倒其他鸟的鸣唱。它们在雨中噤声了。我想象它们在枝上缩着头,雨顺羽毛流到树枝上,细小的鸟爪变得更新鲜。鸟像我一样盼着雨结束,它不明白下雨有什么用处,像下错了地方。雨让虫子们钻回洞里。
雨一点点小了,树冠间透出光亮,雷声在更远处滚动,地面出现更多的溪流。雨停下的时候,我感觉森林里的树比原来看上去多了,树皮像皮革那么厚重。它们站在水里,水渐渐发亮,映现越发清晰的天光。鸟啼在空气中滑落。过一会儿,有鸟应和,包括粗伧的嘎嘎声。鸟互相传话,说雨停了。
这时候,树的上空是清新的蓝天,天好像比下雨前薄了一些,像脱掉了几件衣服。我本来从铁桥那边跑到林中躲雨,我住的符登堡公爵修的旧王宫已经很近。我改变了主意,穿着这身湿衣服继续往熊湖的方向走,这个湖在森林的深处。
空气多么好,青蛙在水洼间纵跳,腿长的像一把折叠的剪刀。小路上,又爬满橙色的肥虫子,我在国内没见过这么肥的虫子。回头看,身后的路上也爬满了虫子,好像我领着它们去朝圣。
路上陆续出现在林中散步的德国人,他们像我一样,被雨挡在森林里。被雨淋过,他们似乎很高兴,脸上带着幸运的笑容。但他们不管路上的虫子,啪啪走过去,踩死许多虫子。他们从不看脚下,只抬着头朝前走。鸟的鸣唱声越来越大,像歌颂雨下得好或停得好。整个森林变得湿漉漉,我觉得仅仅留在树叶上的水就有几百吨。
话说《天龙八部》第三章之中,段誉被初次见面的木婉清折辱一番之后狼狈不堪,经过一座铁索桥重渡澜沧江之后,走了二十多里来到一处小市镇上。
金庸先生写道:
他怀中所携银两早在跌入深谷时在峭壁间失去。自顾全身衣衫破烂不堪,肚中又十分饥饿,想起帽子上所镶的一块碧玉是贵重之物,于是扯了下来,拿到镇上唯一的一家米店去求售。米店本不是售玉之所,但这镇上只有这家米店较大,那店主见他气概轩昂,倒也不敢小觑了,却不识得宝玉的珍贵,只肯出二两银子相购。段誉也不理会,取了二两银子,想去买套衣巾,小镇上并无沽衣之肆,于是到饭铺中去买饭吃。
南诏、大理国时期,云南地区的主要货币是海贝。
《新唐书·南诏传》记载:
(南诏)以缯帛及贝交易,贝之大若指,十六枚为一觅。
这是大理为中心的地区以海贝为货币的最早记录。
大理国时期,根据宋政和年间(相当于段誉在位时期)的《证类本草》卷廿三记载:
贝子,云南极多,用为钱货交易。
1976年,在维修大理崇圣寺(就是《天龙八部》中的天龙寺)千寻塔时,在塔顶基座处发现海贝约38000枚,重达十余公斤。这是云南地区发现贝币最多的一次,也是大理国使用贝币的铁证。
而至今白族语言中,钱还叫做”贝八“,这是语言遗存上的一个证据。
这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探索的问题,云南地区金银铜的矿藏和开采量一直不低,在野史中,大理国开国之主段思平甚至获得了南诏六大宝库中的金银宝库,不使用贵金属而使用海贝作为货币,实在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特别是云南并不濒海,靠海吃海也无从说起。
从海贝的源头考察,或许是一个有益的思路。
据学者研究,大理流通的海贝,主要来自于印度、菲律宾以及台湾、海南岛、西沙群岛等印度洋、西太平洋暖水区域。
历史上,古代印度支那、东南亚和南亚乃至西亚的许多国家都曾经使用海贝为货币,其中以古代天竺(包括今印度和孟加拉)、古代骠国和蒲甘(今缅甸)、古代暹罗(今泰国)、古代吕宋(今菲律宾)的使用尤为普遍。
另一方面,大理使用贝币有其深刻的经济学内涵。
其实中原地区自夏商之际至秦统一中国,海贝作为货币也被使用达1300余年,“至秦废贝行钱”,海贝才退出货币舞台。
但在圆形方孔钱等铸币文明进步的同时,铸币本身带来了铸币税——铸币税是指货币铸造成本低于其面值而产生的差额,因为铸币权通常只有统治者拥有,所以铸币税也是一种特殊而独占的税收收入,是政府的一个较为隐蔽又十分重要的收入来源,在另一个角度,自然是对民众财富的一种转移。
南诏、大理因为僻处边陲,货币形式较为”原始“的同时,反而因祸得福,使得铸币税被降到最低,海贝本身成了一种较为理想的货币形式,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民生福祉。
《天龙八部》第八章写道:
到得傍晚,保定帝换了便装,独自出宫。他将大帽压住眉檐,遮住面目。一路上只见众百姓拍手讴歌,青年男女,载歌载舞。当时中原人士视大理国为蛮夷之地,礼仪与中土大不相同,大街上青年男女携手同行,调情嬉笑,旁若无人,谁也不以为怪。保定帝心下暗祝:“但愿我大理众百姓世世代代,皆能如此欢乐。”
明朝开始,随着云南地区纳入中央政府直接统辖,海贝兑换白银的比值不断下降。
史料记载,元朝末年的至元十九年(1282年),大理地区一两银子合贝三十三索;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升至一百七十索;至天启年间(1621—1627年),涨至二百二十四索。另外,加上海贝“既不胜荷挈,而又易于破坏”(《滇略》),海贝终于退出了货币行列。
如果加上明朝白银总量不断增加(美洲白银进入中国)和海贝总量不断减少(海禁对云南的间接影响)的因素,海贝不断贬值的过程必然是有吏治国家强力参与的色彩。
明代白银问题可参见白银三部曲之黑洞吞噬:美欧财货入明清
这是另一个问题,这里就不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