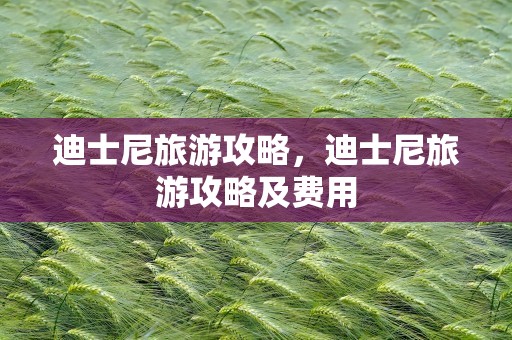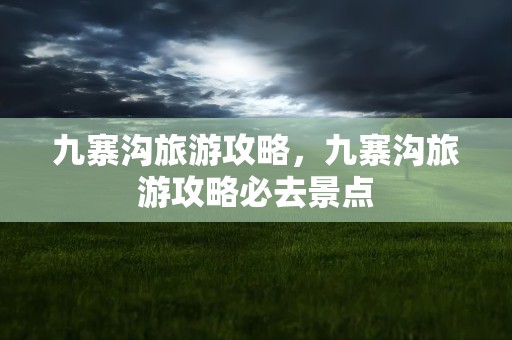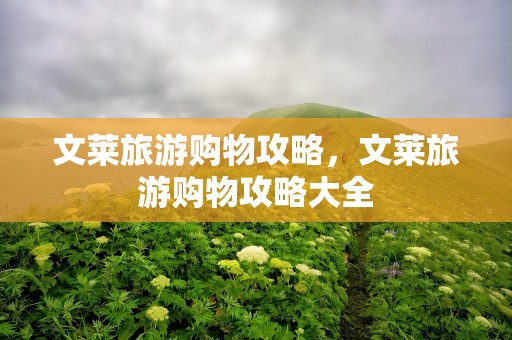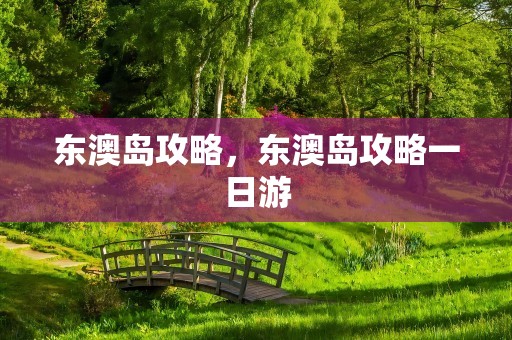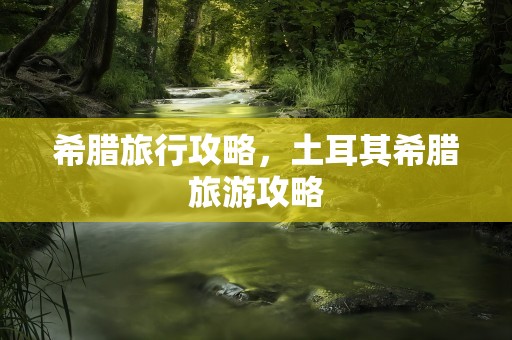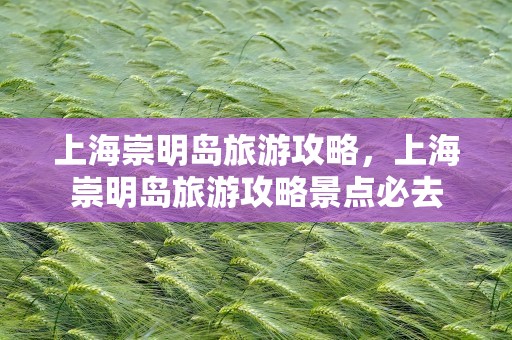成都之所以叫蓉城,主要是因为它来源于一种源产于我国西南地区的芙蓉花,而芙蓉花是成都的市花,所以蓉城指的便是成都。因为成都在五代十国时期遍种芙蓉,成都便因花而得其美名,也称芙蓉城。
都江堰
都江堰位于成都市都江堰市灌口镇,是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子率众于公元前256年左右修建的并使用至今的大型水利工程,被誉为“世界水利文化的鼻祖”。都江堰水利工程,是全世界迄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是全国著名的旅游胜地,也是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附近景色秀丽,文物古迹众多,主要有伏龙观、二王庙、安澜索桥、玉垒关、离堆公园和玉垒山公园等。
青城山青城山位于都江堰市西部,是道教发祥地之一,素有“青城天下幽”之称。分为前山、后山两个景区,前山是青城山风景名胜区的主体,道教文化、文物古迹多集中这里,几乎百步就可看到一座宫观,在茂密的植被覆盖下古典而神秘。后山面积较大,保持了相当原始的风貌,山脚有泰安古镇和泰安寺。宫殿香火虽不如前山,但清幽洁净更胜一筹,适合休闲徒步游。多数游客去的都是前山,后山更适合登山爱好者。
锦里古街锦里古街位于成都市武侯祠附近,是成都知名的步行商业街,由一大片清末建筑风格的仿古建筑组成,拥有数量众多的酒吧、餐饮名店,是西蜀历史上最古老、最具有商业气息的街道。锦里古街洋溢着成都市井特有的喧嚣和随意,街道两边售卖的都是颇具当地特色的物品,手工的皮包、五颜六色的布灯笼等,还有众多老成都手艺人在忙碌,吹糖画、捏面人。夜幕下红灯笼亮起后的锦里,酒吧茶馆喧嚣热闹,其中比较有名的莲花府邸酒吧,据说很多超女、快女都在此唱过歌。
《完美世界》里面很多角色描绘的比较清楚,不仅是主角很多人喜欢,也有反派角色得到很多人的喜欢,其中在完美世界中反派之一安澜就让人恨不起来。
安澜给人留下的人印象就是狂,安澜其实狂是有狂的资本,不朽之王安澜,左手持矛,右手持盾,是九天十地的主宰之一,放眼天下也没有几个人能够入的了他的法眼,安澜对自己的实力,有着无比的自信
为什么安澜的人气这么高,其实刚开始辰东就给了安澜很多的铺垫,还没有登场的时候就给了很多画面,只要是在异界知乎安澜的名字,虚空就会显现他的武器,这也是的安澜的实力的象征,法则的力量,这点可以看出来安澜不仅实力强大,这个性格还是十分的狂妄,颂我真名者,轮回中见永生,只要是直呼他的名字,就可以把一个普通人就可以吓破胆,加上还没有登场时各种人的吹嘘,让道友们当时就一直期望他的登场。
他是荒天帝的敌人,身性多疑,曾经怀疑种子钥匙在罪州,把整个罪州全部的生灵抓去到异域,当时火灵儿也被一起带走,给罪州带来无尽的杀戮,生灵涂炭,在安澜的眼里,罪州的生灵不过是蝼蚁,死了也就死了,自己才是可以掌握他们命运的。
就算自己不敌荒天帝,但是安澜有自己的傲气,这个傲气也不会让自己低头的,就算把自己打死,自己也不会服气。
在石昊刚成为准仙帝的时候,横扫天下,异域的主宰们都不敢得罪他,还有很多人都直接躲了起来。
但是安澜,在明知道不敌的情况下,拿着自己的长枪就来了,虽然自己的实力不如石昊,但是自己的气势一定不能对方压制,就算你现在成荒天帝了,但是我还是不惧,之前你修为不够的时候还不是任由我欺负的,当年我在罪州抓走火灵儿的时候,你不还是不敢得罪我,没有丝毫畏惧。一直到死也从没有屈服,这可能就是安澜的道心吧。
《新唐书地理志》有记,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长江下游水患,大量难民四处逃窜,不知往东乃是“东极陆尽”就停留迁徙在了这个荒岛。总有饱学之士恍然大悟,甚至发现了一些蛛丝马迹可以佐证,荒岛正是距离当时957年前徐福求仙丹途经的“蓬莱”,于是皇帝辗转反侧赐了一个岱山最早的建制称谓“蓬莱乡”。
无独有偶,就在山东渤海之滨唐贞观八年(634)已经始置蓬莱镇,这种重复应该不是当时皇帝的视而不见和疏忽,相反可以断定,关于“蓬莱”真正归属的争论就从那个时代开始了。
奇书《列子·汤问》记载,海上其实有五座仙山,一曰岱屿、二曰员峤、三曰蓬莱、四曰方丈、五曰瀛洲。岱屿和员峤因为飘忽不定难觅踪迹,可能已经流入海底,所以后世只流传有三座仙山。
徐福为求长生不老药出海数年未果,推托说海中有巨大的鲛鱼阻碍,无法远航,要求增派射手对付鲛鱼,秦始皇应允。鲛鱼射杀后徐福再度率众出海最终抵达瀛洲,只顾自己快活成仙,不管秦始皇在杳无音信的等待中英年夭折了。
据说难民栖居蓬莱乡之后借渔盐之利,行舟楫之便,逐渐繁盛起来,但是海域经常不得安宁,海岛时有狂风大作,波澜泛滥,巨浪碎石,茅屋吹散,地动山摇……所以就想到了鲛鱼作恶的传说,于是在渔港高处建了一亭,用作瞭望鲛鱼的兴风作浪,随时鸣钟警报,渔船闻讯立刻折返,收帆歇渔。
但是有远见卓识的人开始不满足了,请来隐居深山的道士作法震慑鲛鱼,道士卜了一卦说,鲛鱼是仙山守护,你们不应该随便占了“蓬莱”啊!说完仅留了一张黄纸符箓,画有“安澜”两字天书便拂袖而去。“安澜”符箓贴在高处一亭,平静了好一阵,直到一道闪电一场暴雨毁掉了那个亭子,符箓上的天书也化作了泥水,淹没了所有的田宅,人们的脸上分不清雨水还是泪水,再次流离失所,再次一无所有,只能再次迁徙。
就在人们绝望的那一刻,一个小沙弥背着一尊玉观音渡上了岸,洁白无瑕的玉佛用一件旧袈裟包裹着,打开的那一瞬在烛光里折射着玲珑,映透半边黑夜。雨停了,潮退了,海水也平静了。
一直到《岱山县志》中说宋端拱二年(989)置岱山盐场;是年,建岱山庙,以祀隋朝征流求将军陈棱。关于“蓬莱”几百年归属争论才有了官方的强制性的结论,“蓬莱乡”才有了一个沿用至今的新名字“岱山”。之后,因为史料的严重匮乏又开始了旷日持久的“岱山”出处之考,再次成了一场喋喋不休口水仗的谜团。大部分文人学者更倾向于“岱岳”之称的沿袭之说,“海上泰山”的光环照耀着整个岱山,谁不愿意佩戴上“五岳之尊”这样的光环?哪怕是虚荣的牵强附会的。
恰恰在此时,人们早已忘记了传说中已经消失的“岱屿和员峤”,而“岱屿”为什么就不能更确切呢?一座消失的或者说仍然在飘忽不定的仙山?不用修饰,不用引经据典,直译就是“岱山岛”的意思。
二
大约二十五年前,安澜路镌刻在我脑海一隅,很是醒目,经常可以想起这两个字,一直在推敲为什么会用这两个字。直到逐渐了解了岱山史志,可以追溯到徐福跣足登岸,发现了这片岛屿,并且自认为这就是蓦然回首的“蓬莱”。也包括某些口口相传的,甚至是假设的历史,我们冠以传说的雅号。
传说不一定就是胡说,野史不一定就不是历史了。但是安澜路的由来真的是无从考证,所以我认为那是符箓,是链接传说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们祈祷大海风平浪静可以扬帆远行;人们祈求海洋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渔业资源可以换来财富;人们祝福世世代代可以在这片古老的仙境里繁衍生息;人们甚至用“安澜路”这三个字横亘高亭,封印传说中的鲛鱼,哪怕凡人犯了天规肆意占了这仙境。
有人反驳,“安澜路”是新中国解放之后的产物,但是在那个三反五反破除四旧的年代,“安澜路”为何没有被贴上“迷信”的标签拿出来游街批斗?难道岱山是与世隔绝跳出三界的桃源异域?
因此我们不妨大胆假设这条“安澜路”的持久生命力,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人们从来没有割断传承祝福的信奉,从来没有放弃对大海的敬畏。
三
第一次漫步安澜路的记忆已经是泛黄的照片,那是朋友骑着自行车带着我穿梭在迷宫一样的小巷,此时回忆摇摆颠簸在青石板铺成的小路依旧是那么清晰,空气像透明的液体,阳光像崭新的颜料,我如今依旧陶醉,恍若昨日。
冷不丁朋友来了一句,这就是安澜路。来不及回神,自行车已经飞快横穿了那条据说最繁华的街市,好比上海的南京路,好比北京的王府井……我的好奇曾在这里定格。
翌日,我一个人摸索着来到安澜路,从一端海堤的尽头出发直逼高亭腹地。那是一个渔船锈迹斑驳,海堤残垣断壁的尽头,记载了时间的沧桑,记载了人与海的相濡以沫,记载了渔夫不惜用生息繁衍来拥抱大海的侵蚀。
这一切都印证了在更久远的时间横截面里,这里曾是拥挤不堪的渔港和攘来熙往的鱼市。渔火簇拥时分便有大批渔夫挑着满满腾腾鱼货上岸,四处吆喝此起彼伏,把安澜路交汇沿港路的尽头点燃成夜幕旷宇里一颗繁星。现在最热闹的要算“歇渔节”那天了,沿港路两旁早已扎起了巨型灯车、各式花灯、万鱼灯笼……吃了晚饭“踩街”的人如潮水一般从沿港路两头朝着居中的安澜路鱼贯而入。
突然沿港路跟安澜路交汇的三角地带伴着锣鼓喧天传来一片欢呼声,来的是舞龙队和舞狮队。舞龙围成一圈,舞狮分四方各一侧,稍中间就是穿着十八人物戏服踩着高跷粉墨登场了,正中间三人分别装扮成金刚、力士、神兽,带着彩绘面具手舞足蹈跳着傩戏。跳傩自北向南流传,旨在酬神还愿,结合岱山海坛举行的“休渔谢洋大典”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海洋民俗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