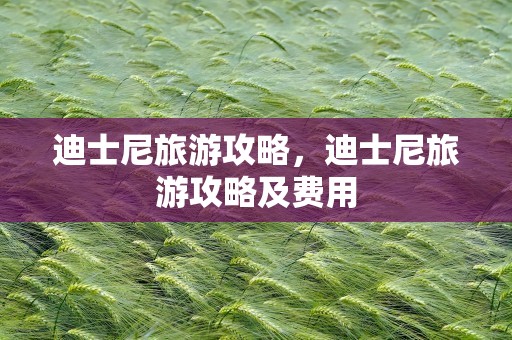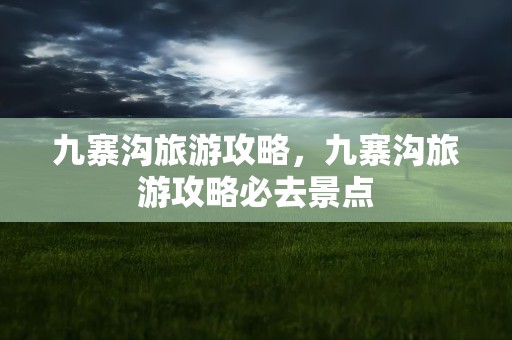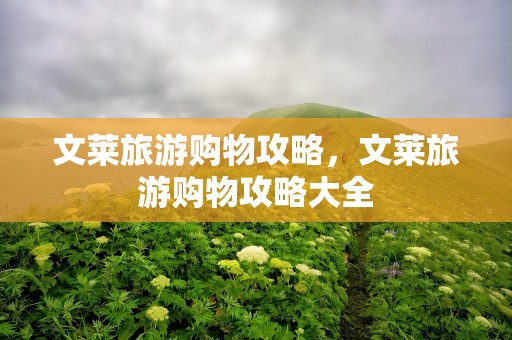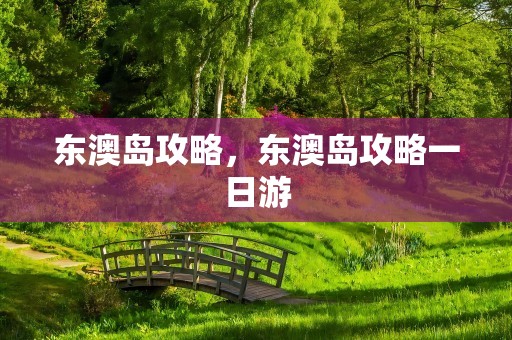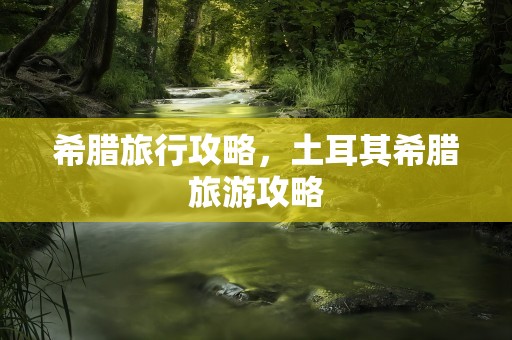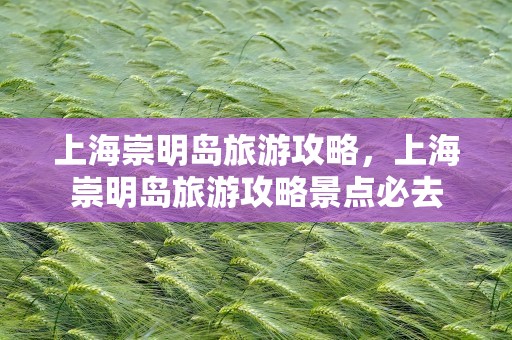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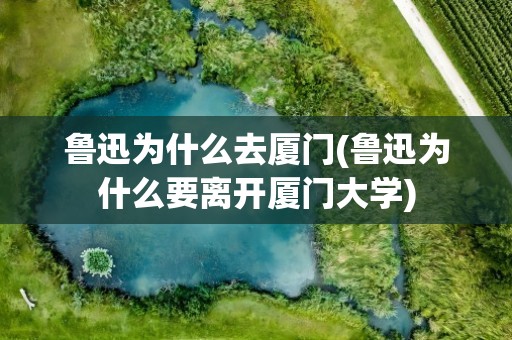
第一、水土不服
我们来后,都被搁在须作陈列室的大洋楼上,至今尚无一定住所。听说现正赶造着教员的住所,但何时造成,殊不可知。我现在如去上课,须走石阶九十六级,来回就是一百九十二级;喝开水也不容易,幸而近来倒已习惯,不大喝茶了……店中人能说几句"普通话",但我懂不到一半。
这里的人似乎很有点欺生。因为是闽南了,所以称我们为北人;我被称为北人,这回是第一次。现在的天气正像北京的夏末,虫类多极了,最利害的是蚂蚁,有大有小,无处不至,点心是放不过夜的。
蚊子倒不多,大概是因为我在三层楼上之故。生疟疾的很多,所以校医给我们吃金鸡纳。霍乱已经减少了。但那街道,却真是坏,其实是在绕着人家的墙下,檐下走,无所谓路的。——两地书•四二
但饭菜可真有点难吃,厦门人似乎不大能做菜也。饭中有沙,其色白,视之莫辨,必吃而后知之。我们近来以十元包饭,加工钱一元,于是而饭中之沙免矣,然而菜则依然难吃也,吃它半年,庶几能惯欤。
又开水亦可疑,必须自有火酒灯之类,沸之,然后可以安心者也。否则,不安心者也。——19261003致章廷谦
我想厦门的气候,水土,似乎于居民都不宜,我所见的本地人,胖子很少,十之九都黄瘦,女性也很少有丰满活泼的;加以街道污秽,空地上就都是坟,所以人寿保险的价格,居厦门者比别处贵。——两地书•九三
第二、不服校长作风
鲁迅先生为什么离开厦大呢?据我们当时的了解,他对“英国籍的中国人”、尊孔的林文庆校长,对排挤国学院的敦务长刘树杞,以及国学院的一批“现代评论”派之流人物,感到不满,甚至憎恶。
他与学校当局根本冲突,已到了无可谓和的地步。在十二月底,他坚决地向学校提出辞职书。学校当局对他的辞职书,感到很难弄。——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
另外我还知道:学校当局连同从北京来的一部分人土,都主张学生应该钻进实验室埋头研究,百事不管;鲁迅先生却公开演说,劝学生要留心世事,出来做“好事之徒”。
校长尊孔,鲁迅先生却劝学生要少读中国书。别人都去巴结校长,企图做“永久教授”,鲁迅先生却一定要走。校长要学生静,鲁迅先生却希望学生动。弄来弄去,总不对头。——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
第三、不服顾颉刚等人
看厦大的国学院,越看越不行了。朱山根是自称只佩服胡适陈源两个人的,而田千顷,辛家本,白果三人,似皆他所荐引。白果尤善兴风作浪,他曾在女师大做过职员,你该知道的罢,现在是玉堂的襄理,还兼别的事,对于较小的职员,气焰不可当,嘴里都是油滑话。
我因为亲闻他密语玉堂,"谁怎样不好"等等,就看不起他了。前天就很给他碰了一个钉子,他昨天借题报复,我便又给他碰了一个大钉子,而自己则辞去国学院兼职。我是不与此辈共事的,否则,何必到厦门。
我原住的房屋,要陈列物品了,我就须搬。而学校之办法甚奇,一面催我们,却并不指出搬到那里,教员寄宿舍已经人满,而附近又无客栈,真是无法可想。
后来总算指给我一间了,但器具毫无,向他们要,则白果又故意特别刁难起来(不知何意,此人大概是有喜欢给别人吃点小苦头的脾气的),要我开帐签名具领,于是就给碰了一个钉子而又大发其怒。大发其怒之后,器具就有了,还格外添了一把躺椅,总务长亲自监督搬运。
因为玉堂邀请我一场,我本想做点事,现在看来,恐怕是不行的,能否到一年,也很难说。——两地书•四六
我在厦门时,很受几个“现代”派的人排挤,我离开的原因,一半也在此。但我为从北京请去的教员留面子,秘而不说。不料其中之一,终于在那里也站不住,已经钻到此地来做教授。此辈的阴险性质是不会改变的,自然不久还是排挤,营私。——19270420致李霁野
营植排挤,本是三根惟一之特长,我曾领教过两回,令人如穿湿布衫,虽不至于气绝,却浑身不舒服,所以避之惟恐不速。但他先前的历史,是排尽异己之后,特长无可施之处,即又以施之他们之同人,所以当他统一之时,亦即倒败之始。
但现在既为月光所照,则情形又当不同,大约当更绵长,更恶辣,而三根究非其族类,事成后也非藏则烹的。此公在厦门趋奉校长,颜膝可怜,迨异己去后,而校长又薄其为人,终于不安于位,殊可笑也。
现在尚有若干明白学生,固然尚可小住,但与月孽争,学生是一定失败的,他们孜孜不倦,无所不为,我亦曾在北京领教过,觉得他们之凶悍阴险,远在三根先生之上。和此辈相处一两年,即能幸存,也还是有损无益的,因为所见所闻,决不会有有益身心之事。——19350108至郑振铎
第四、好友孙伏园的离去
由此可见鲁迅与厦大之间矛盾颇多,鲁迅因此曾在书信中直言不讳地说“厦大是废物,不足道了”。不论如何这主要是鲁迅与校方的矛盾,与学生之间并没有什么冲突,鲁迅在厦大是一如既往地深受学生爱戴,而鲁迅也努力教学、帮助青年。
鲁迅(1881年9月25日~1936年10月19日),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字豫才,浙江绍兴人。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教育家、民主战士,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早年与厉绥之和钱均夫同赴日本公费留学,于日本仙台医科专门学校肄业。“鲁迅”,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所用的笔名,也是最为广泛的笔名。
鲁迅一生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思想研究、文学史研究、翻译、美术理论引进、基础科学介绍和古籍校勘与研究等多个领域具有重大贡献。
他对于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发展具有重大影响,蜚声世界文坛,尤其在韩国、日本思想文化领域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被誉为“二十世纪东亚文化地图上占最大领土的作家”。
张映勤一九一二年五月初,
鲁迅随教育部从南京迁到北京供职,直到一九二六年八月南下赴厦门教书,在北京共生活了十四年,当然这也是他在教育部公务员生涯的十四年。
北京是鲁迅的第二故乡,是他除绍兴之外生活得最久的地方,与朋友多次谈起北京总是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他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中国乡村和小城市,现在恐无可去之处,我还是喜欢北京,单是那一个图书馆,就可以给我许多便利。”去世前的几个月,鲁迅还认为:“我很赞成你们再在北平聚两年;我也住过十七年,很喜欢北平。现在走开了十年了,也想去看看,不过办不到,原因,我想,你们是明白的。”(致颜黎民信)。
鲁迅喜欢北京自然有他的理由:
其一,他的亲人都在北京。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底,鲁迅将全家老小,自己的母亲鲁瑞、妻子朱安及三弟周建人一家接到北京,与二弟周作人一家同住于八道湾胡同十一号,周氏三兄弟,除两年以后三弟周建人只身到上海谋生之外,全家三代十几口人都在北京生活。
其二,他的职业在北京。从三十二岁到四十六岁,这十四年的黄金岁月,鲁迅一直在教育部当职员,任科长、佥事,工作清闲无聊,有时间创作研究和教书,除了工资收入,尚有讲课费和稿费、版税,这是他能坚持十四年始终没有跳槽的主要原因。
其三,他的事业在北京。北京是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鲁迅的新文学创作从这里起步、成熟,他的文学创作、译介研究都集中在北京时期,并先后在八个学校兼课,从而奠定了他成为精神领袖和文学大师的地位。北京做过八百多年的帝都,恢弘大气,精英荟萃,文化资源丰富,学术氛围浓厚,思想活跃,信息畅通,图书馆、大学、报刊、书店林立,为鲁迅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方便有利的条件,北京是他大展身手的绝好舞台。
其四,他的活动圈子和朋友圈子也主要集中在北京,这些人包括思想文化界名人,学校任教的同事、学生,社团报馆的编辑、文学青年等等。鲁迅与他们相互影响、相互激励,这些朋友和文化圈子是鲁迅成长发展的肥沃土壤。
鲁迅在自己写的《自传》中这样解释道:“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西滢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
先说撤职一事。鲁迅参与了北师大的学潮,始终支持学生与当时的教育总长章士钊、北师大的女校长杨荫榆做斗争,为此,章士钊呈请段祺瑞批准将鲁迅撤职,此事发生在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二十二日鲁迅向平政院投递控告章士钊的诉讼,打了平生第一场官司。但同年十一月章士钊被免去教育总长职务,转年的一月十六日新任命的教育总长易培基,支持学生,同情鲁迅,取消了这个违法的撤职令,三月中旬官司胜诉,鲁迅官复原职,撤职风波就此平息。这件事不会直接导致鲁迅离京,但因此与教育部关系弄僵却是事实。
再说逮捕一事。在“三一八惨案”中,鲁迅奋笔直书,与段祺瑞政府进行了不懈的抗争,社会上传闻,报纸上也刊出名单,政府要通辑第二批“暴徒首领”四十八人,鲁迅在册,名列第二十一名,他自三月二十六日起离家避祸。但当时的北京政局多变,一个月后,奉军进京,段祺瑞下台,被通缉的威胁消除了,五月初,鲁迅回到家里,可以从容自由地活动了,离京之前,他还多次参加朋友送别的宴请,通辑逮捕之事早已化为乌有。
最后说敌人一事。鲁迅在北京期间,与官僚政客、帮闲文人打了几次笔仗,对复古派、学衡派、鸳鸯蝴蝶派、现代评论派都进行过斗争,颇得罪了一些人,最引人注目的是在女师大学潮中与陈西滢的论战,他以一人之力,一管之笔,左右开弓,与周围所有的政客文人开战,树敌确实不少,但是以鲁迅的声望地位、社会影响,更由于他顽强不屈的性格,岂是轻易能让论敌排挤走的,他不可能为了躲避所谓“文人学者”的围攻而不战自退、逃之夭夭。
由此可见,鲁迅离开北京的原因和上面所说的不能说没有一点关系,但决不是主要原因,起决定性因素的另有不便明言的个人隐情,这就是为了追求爱情,为了和许广平开始新的生活,为此,他才选择了离开北京。
毋庸讳言,鲁迅当时是有妻子的,只是与这位名叫朱安的妻子感情不和,两人有夫妻之名,无夫妻之实,结婚近二十年,他在家里过的是孤身生活。一九二五年三月,他在北师大的学生许广平闯入他的生活,两人后来确定恋爱关系,离开北京正是他们商议的结果。许广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要的钱。”虽然后来约定的时间没能守住,但他们确是精心策划过此事。
鲁迅当时的收入主要是工资、讲课费、稿费和版税,虽谈不上富足,但绝对在中产以上,为了将来与爱人开始新的生活,必要的经济准备是不可少的。就各方面的条件而言,他继续留在北京自然不成问题,但是如果要和许广平结合,继续留在北京显然就成了问题。
首先,妻子和母亲都在北京。他虽然不接受朱安,却也无意伤害对方,没打算过遗弃妻子。只能把这个母亲送给他的“礼物”返还给母亲,让朱安留在家里照顾堂前。自然,自己另有所爱,以朱安温顺平和的性格不至于因此而闹出大的风波,但是同时要在北京维持两个家庭显然多有不便。
其次,当时,他与二弟周作人失和已经三年,兄弟恩断义绝,反目成仇,这种精神打击对鲁迅是致命的,他们在北京共同奋斗了十多年,志趣相投、感情深厚、合作融洽,手足情断让他刻骨铭心、痛心疾首。两人有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亲人,共同的朋友。失和以后,再无直接交往,许多朋友聚会宴请,鲁迅都刻意回避周作人而拒绝参加。当然,以周作人的品性,对“有妇之夫”的鲁迅和学生许广平的关系肯定不会认可,为了摆脱尴尬的局面,他在内心深处也许未必愿意和周作人在一个城市生活。
另外,鲁迅自然不会畏惧别人的蜚短流长,但是他的生活圈子就在北京,有过多重的文化身份:政府职员、大学讲师、自由作家、编辑家和文学活动家。此地的亲朋好友、学生同行,熟人众多,自己名冠京华,早已成为人所瞩目的公众人物,关于他的个人生活,势必会遭到世俗舆论的非难与压力,无论是善意的议论,还是恶意的攻击,人们说长道短背后议论,甚至流言蜚语都是免不了的,这些非议,鲁迅和许广平不能不有所顾忌。
上面这些因素,至少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鲁迅如果和许广平结合,继续生活在北京显然有诸多不便、诸多麻烦,与其身处是非之地,不如远走高飞,到一个新的环境开始新的生活。北京他不是不能待,而是他不想待,不愿待。
正是为了追求爱情和许广平到外地开始新的生活,鲁迅这才决定离开北京。
因为与反动派的冲突,迫使他离开中山大学,离开厦门大学是因为所写的文章,直插国民党政府罪恶的心脏,被驱逐出校。
此文集作为“回忆的记事”,多侧面地反映了作者鲁迅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形象地反映了他的性格和志趣的形成经过。
揭露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种种丑恶的不合理现象,同时反映了有抱负的青年知识分子在旧中国茫茫黑夜中,不畏艰险,寻找光明的困难历程,以及抒发了作者对往日亲友、师长的怀念之情。
扩展资料:《朝花夕拾》十篇散文勾勒了从清末到辛亥革命时期的若干社会生活风貌,是一幅幅世态图和风俗画。虽然是回忆性散文,但是有现实的斗争性和深邃的思想性,蕴含着作者对历史的深刻思考和对现实的执着态度。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和《五猖会》中鞭挞了封建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对儿童活泼可爱的天性的束缚、压制和摧残;
《无常》一文中采用《聊斋志异》的讽刺笔法,揭露了人间没有公正的裁判,嘲讽了那些打着“公理”、“正义”旗号的“正人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