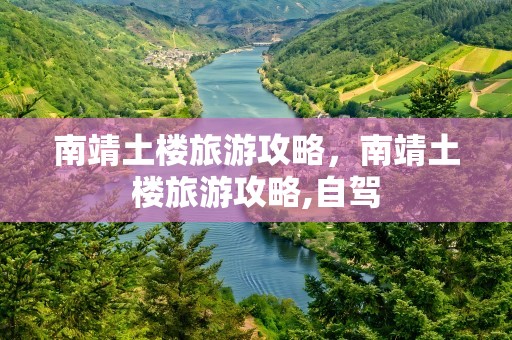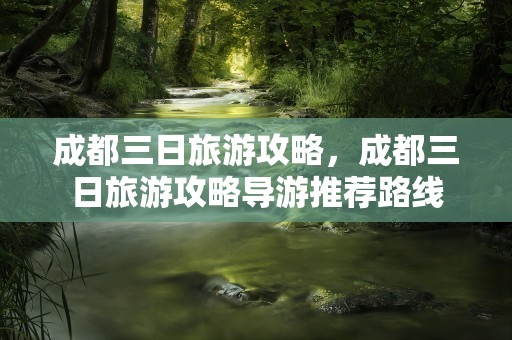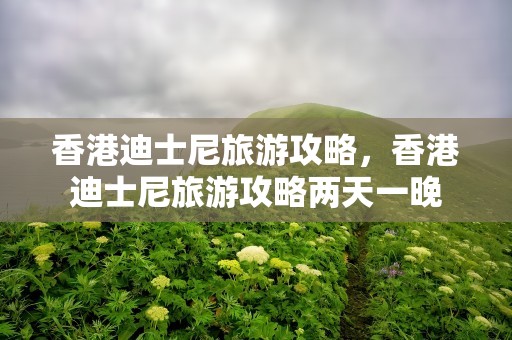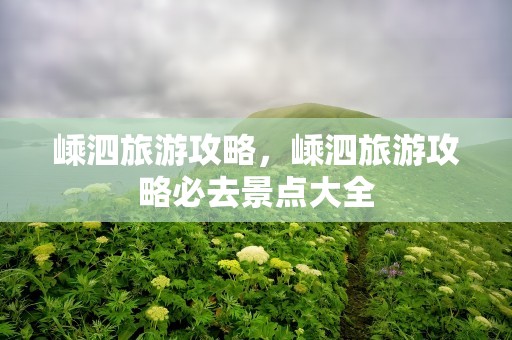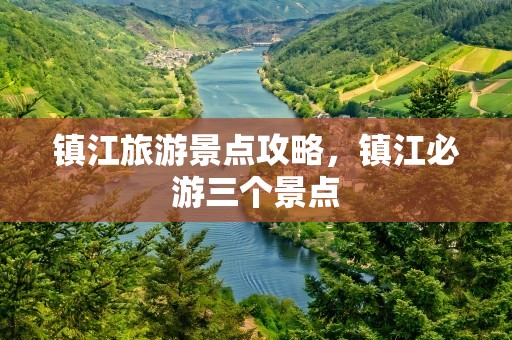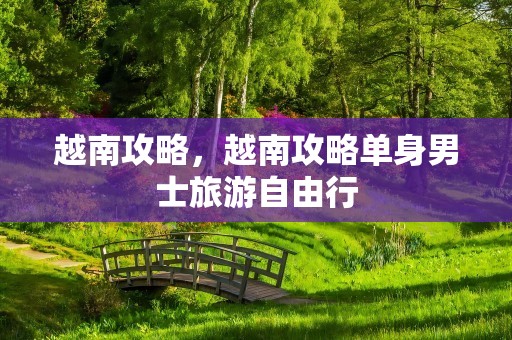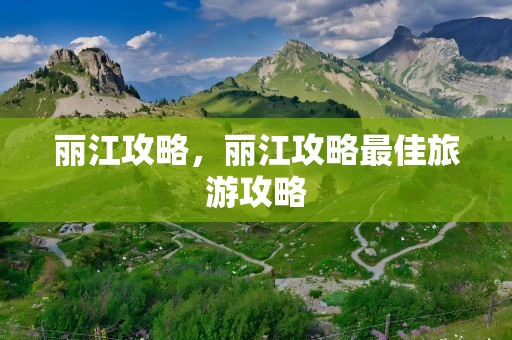浆加了酱油,为什么会凝成白花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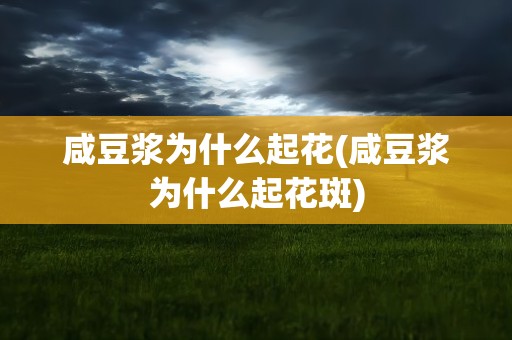
许多人都爱喝豆浆。
有的人爱喝甜豆浆,有的人爱喝咸豆浆。
喝甜豆浆的人,在豆浆中加些白糖,豆浆依然象牛奶一样,啥样子也没有变,只是味道变甜了。可是喝咸豆浆的时候,怪事就发生了,同样是象牛奶一样的豆浆,加进酱油以后,却很快地凝成了白花花的一碗。这是什么道理呢?
大家知道,豆浆是用黄豆做的。
当黄豆浸泡磨碎,加适量的水以后,黄豆中的大部分蛋白质、无机盐和部分水溶性维生素,都高高兴兴地送到水去了。只有脂肪是不溶于水的。幸亏蛋白质有一种奇特的本领,能够把油脂乳化成很小的油滴,而自己包在小油滴外面,“保护”油滴彼此不会合并,而浮悬在水中。
所以说,豆浆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和脂肪,当然也有一些无机盐和维生素。
而酱油呢?除了一些氨基酸等物质外,还含有许多食盐。怪不得酱油吃起来挺咸。
豆浆中加进酱油,食盐和蛋白质就碰头了。食盐原是蛋白质的冤家对头,它一进入豆浆,就会迫使蛋白质从水中沉淀出来。这是什么道理呢?
原来蛋白质溶在水中以后,就成为一种胶体溶液,蛋白质胶体微粒是靠了两件“法宝”使自己不会沉淀出来的。一个是蛋白质胶粒会将溶液中的一部分水“拉”到自己的周围,形成一个水化层,当蛋白质胶粒在水中运动时,是带着这个水化层一起运动的,这样,当两个蛋白质胶粒相遇时,由于水化层的阻挡,使两个胶粒不会合在一起。另一个“法宝”是,蛋白质胶粒会通过自己的电离和吸附溶液中的某一种带电离子在自己周围,使自己带上电荷。这样当两个蛋白质胶粒相遇靠近时,由于每一个胶粒所带的电荷都是同一种类型的,因为电荷相同就相互排斥,迫使两个胶粒又重新分开。
这样,蛋白质胶粒就可以安安稳稳的在水中“游荡”了。
可是加入食盐后,情况就不同了。原来食盐是个电解质,它在水中会电离成带正电的钠离子和带负电的氯离子。这些离子吸引水分的能力都比蛋白质胶粒来得强,因此它们不但吸引溶液中的水分子,而且把蛋白质胶粒周围的水化层中的水分子也“抢”过来,使水化层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假如蛋白质胶粒是带正电的,那么电解质解离出来的负离子就会“挤”到蛋白质胶粒周围,结果使蛋白质胶粒所带的电荷被“中和”了。蛋白质胶粒借以使自己稳定的两个“法宝”都破坏了,这时当两个蛋白质胶粒再碰头时,就会合并在一起,一并两并蛋白质胶粒就会越变越大,最后就从水溶液中沉淀出来了。
豆浆加酱油后出现的白花花,就是沉淀出来的蛋白质。做豆腐时向豆浆中入盐卤或石膏,道理也和上面讲的一样。
豆子不同,用安徽产的黄豆,那个黄豆容易出花,还有,多放点豆子,少放点水,我发觉,我们用的豆浆机可能做出来的有点淡,所以出花有点难度,安徽黄豆,你淘宝上买,找安徽的卖家,我就这样的。酱油放好,你豆浆冲下去的时候,稍微细条一点往下浇,像豆浆店那样,试试,反正我出花的概率也不高的。
南方和北方最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叫做豆花儿,我们叫做豆腐脑。南甜豆花与北咸豆脑之战、就像是肉粽与糖粽之战一样激烈。有位杭州朋友来东北旅游,他早上去早市吃完这一碗东北的面条,说这个面条为什么是酸的呢,而南方的面条是碱味的。
说起豆浆豆花是甜的,有一个南方朋友说人从小只吃咸豆浆,咸豆花,肉粽,肉包,不喜欢吃甜食,不仅是南北的口味差异,就连隔壁的村子都会有口味的差异,人间的风味就存在熙熙攘攘的市井当中。
南北饮食差异比较大,甜豆浆还是咸豆浆可以说是世纪争议。东北人的品味是偏咸口,甜的菜品也并不是很多。但是东北豆浆是甜的,却不是咸的,但是豆腐脑是咸的,不过豆腐脑里面放的是卤汁,不是加盐。
豆浆+油条,黄金搭配,把油条放进豆浆里吃,掰一掰、沾一沾、泡一泡。然后一口吃下去,简直就是人间美味啊。
豆腐脑是一种很神奇的食物,豆浆到豆腐脑的华丽变身,从液体变为固体,是一场不可回头的旅行。豆腐脑儿配油糕,每天叫醒东北人的不是早晨,而是那些香气扑鼻的早餐!在南方时,豆腐花大约就是和豆腐脑是同一种类了,但味道相差甚远,甜咸口味完全不同,也只有回到北方才能吃上这么一碗地道的豆腐脑了。
豆腐脑里面放的是卤汁,小时候,卤汁里面的内容丰富,有水发的黄花菜、木耳,鸡精等。小时候,我记得特别爱吃豆腐脑,那时候走街串巷,有一个卖豆腐脑的,一到中午就挑着担子来了,放假一到中午十一点的时候,我就下楼去买,那时候卤汁挺丰富,但现在基本上看不到实货了,就剩汁了。一般卖豆腐脑的铺子儿,还备有韭菜花儿、葱末、辣椒油、香菜末、蒜汁儿等,各人根据自己口味儿选择放什么。